67еҗҚе·ҘзЁӢзЎ•еЈ«д»Ҙе®һи·өжҲҗжһңж•ІејҖеӯҰдҪҚжҺҲдәҲеӨ§й—Ё
еҸ‘зЁҝж—¶й—ҙпјҡ2025-08-04 09:45:00 жқҘжәҗпјҡ дёӯеӣҪйқ’е№ҙжҠ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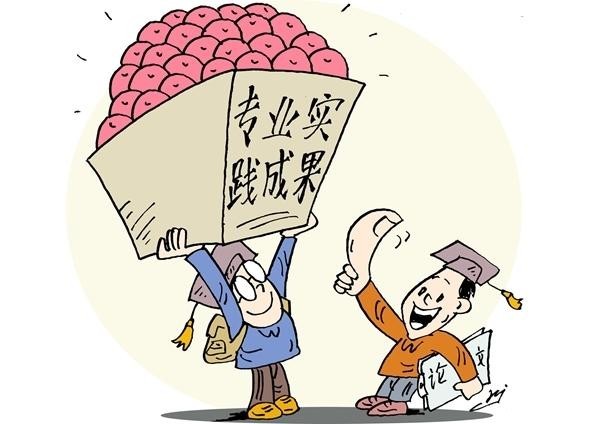
гҖҖгҖҖи§Ҷи§үдёӯеӣҪдҫӣеӣҫ
гҖҖгҖҖгҖҠдёӯеҚҺдәәж°‘е…ұе’ҢеӣҪеӯҰдҪҚжі•гҖӢпјҲд»ҘдёӢз®Җз§°вҖңеӯҰдҪҚжі•вҖқпјүиҮӘд»Ҡе№ҙ1жңҲиө·жӯЈејҸж–ҪиЎҢгҖӮеңЁеӯҰдҪҚжі•иөӢдәҲе®һи·өжҲҗжһңдёҺеӯҰдҪҚи®әж–ҮеҗҢзӯүжі•еҫӢең°дҪҚзҡ„е…ғе№ҙпјҢе…ЁеӣҪйҰ–жү№вҖңеҗғиһғиҹ№вҖқзҡ„67еҗҚе·ҘзЁӢзЎ•еЈ«пјҢз”ЁдәІжүӢи®ҫи®Ўзҡ„иЈ…еӨҮгҖҒзј–еҶҷзҡ„иҪҜ件е’ҢдјҳеҢ–зҡ„е·Ҙиүәж–№жЎҲпјҢж•ІејҖдәҶеӯҰдҪҚжҺҲдәҲзҡ„еӨ§й—ЁгҖӮ
гҖҖгҖҖеңЁд»Ҡе№ҙйҰ–жү№жҜ•дёҡзҡ„2100еӨҡеҗҚдё“йЎ№иҜ•зӮ№е·ҘзЁӢзЎ•еЈ«дёӯпјҢд»Ҙе®һи·өжҲҗжһңз”іиҜ·еӯҰдҪҚзҡ„еҸӘжңү67дәәпјҢеҚ жҜ”3%е·ҰеҸігҖӮз”Ёж•ҷиӮІйғЁеӯҰдҪҚз®ЎзҗҶдёҺз ”з©¶з”ҹж•ҷиӮІеҸёпјҲд»ҘдёӢз®Җз§°вҖңж•ҷиӮІйғЁз ”究з”ҹеҸёвҖқпјүеүҜеҸёй•ҝйғқеҪӨдә®зҡ„иҜқиҜҙпјҢиҝҷдёӘзңӢдјјдёҚеӨ§зҡ„жҜ”дҫӢпјҢжҳҜдёҖж¬ЎвҖңз ҙеҶ°д№Ӣдёҫ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иҝҷж¬Ўз ҙеҶ°пјҢжҳҜ21жүҖй«ҳж ЎеңЁж— е…ҲдҫӢеҸҜеҫӘзҡ„жғ…еҶөдёӢпјҢж‘ёзҙўеүҚиЎҢзҡ„иү°йҡҫж—…зЁӢгҖӮ
гҖҖгҖҖжү“з ҙеӣәеҢ–зҡ„еӯҰжңҜиҜ„д»·дҪ“зі»
гҖҖгҖҖдҪңдёәе…ЁеӣҪйҰ–жү№д»Ҙе®һи·өжҲҗжһңе®ҢжҲҗеӯҰдёҡзҡ„дё“йЎ№иҜ•зӮ№е·ҘзЁӢзЎ•еЈ«д№ӢдёҖпјҢдёӯеӣҪзҹіжІ№еӨ§еӯҰпјҲеҢ—дә¬пјүе’ҢдёӯеӣҪзҹіеҢ–зҹіжІ№е·ҘзЁӢжҠҖжңҜз ”з©¶йҷўиҒ”еҗҲеҹ№е…»зҡ„2022зә§зЎ•еЈ«з”ҹеј зҷҫе·қжӢҝеҮәжқҘзҡ„жҲҗжһңпјҢжҳҜдёҖз§ҚиғҪжӣҝд»Јдј з»ҹжқҗж–ҷзҡ„вҖңзҺҜдҝқеһӢжҠ—й«ҳжё©йҷҚж»ӨеӨұеүӮ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вҖңйңҖеҗҢж—¶ж”»е…ӢжҠ—180в„ғй«ҳжё©гҖҒиҖҗйҘұе’ҢзӣҗгҖҒйҷҚдҪҺй’»дә•ж¶Ій»ҸеәҰгҖҒйҷҚжң¬15%гҖҒж»Ўи¶іеӣҪ家жө·жҙӢжҺ’ж”ҫж ҮеҮҶзҡ„дә”йҮҚе…іеҚЎгҖӮвҖқйқўеҜ№дёҘиӢӣзҡ„иЎҢдёҡж ҮеҮҶпјҢеј зҷҫе·қи§үеҫ—вҖңж—ўеҝҗеҝ‘еҸҲе…ҙеҘӢвҖқгҖӮеҰӮд»ҠпјҢд»–еҸӮдёҺз ”еҸ‘зҡ„иҝҷз§ҚжҠ—й«ҳжё©йҷҚж»ӨеӨұеүӮе·Із»ҸвҖңдёӯиҜ•иҫҫж ҮпјҢйҖҡиҝҮйүҙе®ҡвҖқпјҢеҚіе°ҶејҖеұ•зҺ°еңәйӘҢиҜҒе·ҘдҪңгҖӮ
гҖҖгҖҖвҖңеӯҰж ЎжҺўзҙўе·ҘзЁӢзұ»дё“дёҡеӯҰдҪҚз ”з©¶з”ҹд»Ҙе·ҘзЁӢе®һи·өжҲҗжһңз”іиҜ·еӯҰдҪҚзҡ„иҜ„д»·жңәеҲ¶ж”№йқ©пјҢдёәжҲ‘们йҮҸиә«жү“йҖ дәҶе®һи·өжҲҗжһңз”іиҜ·еӯҰдҪҚзҡ„е·ҘдҪңжөҒзЁӢдёҺиҖғж ёж ҮеҮҶгҖӮвҖқеј зҷҫе·қиҜҙгҖӮд»Ҡе№ҙпјҢд»–еҫ—д»Ҙз”ЁиҝҷйЎ№е®һи·өжҲҗжһңпјҢйЎәеҲ©иҺ·еҫ—дәҶеӯҰдҪҚгҖӮ
гҖҖгҖҖйқўеҜ№еӯҰдҪҚжі•ж–°еўһзҡ„е®һи·өжҲҗжһңз”іиҜ·йҖҡйҒ“пјҢеӨҡжүҖй«ҳж Ўд»ҚеңЁж‘ёзҙўдёӯгҖӮеӨ©жҙҘеӨ§еӯҰз ”з©¶з”ҹйҷўеӯҰдҪҚеҠһе…¬е®Өдё»д»»еҲҳеәҶеІӯе‘ҠиҜүдёӯйқ’жҠҘВ·дёӯйқ’зҪ‘и®°иҖ…пјҢдёәдәҶжҸҗдҫӣй…ҚеҘ—дҝқйҡңпјҢеӨ©жҙҘеӨ§еӯҰеҜ№йҰ–жү№е®һи·өжҲҗжһңз”іиҜ·иҖ…жҸҗдҫӣ专家йүҙе®ҡиЎҘиҙҙпјҢ并дёҺеӨ©жҙҘеёӮж•ҷ委еҚҸеҗҢе»әз«ӢеӯҰдҪҚи®әж–ҮжҠҪжЈҖдҝқйҡңжңәеҲ¶гҖӮ
гҖҖгҖҖеҲҳеәҶеІӯи§ЈйҮҠпјҢд»Ҙе®һи·өжҲҗжһңз”іиҜ·еӯҰдҪҚпјҢе°ұжҳҜиҰҒйҮҚжһ„е·ҘзЁӢж•ҷиӮІд»·еҖјеҸ–еҗ‘пјҢжҠҠеӯҰдҪҚжҺҲдәҲж ҮеҮҶпјҢдёҺеӯҰз”ҹвҖңи§ЈеҶіеӨҚжқӮе·ҘзЁӢй—®йўҳд»ҘеҸҠеӣҪ家жҲҳз•ҘйңҖжұӮе…ій”®йўҶеҹҹж ёеҝғжҠҖжңҜеҚҮзә§зҡ„е®һи·өеҲӣж–°иғҪеҠӣвҖқзҙ§еҜҶз»‘е®ҡгҖӮд»–жҸҗеҲ°пјҢеӨ©жҙҘеӨ§еӯҰеҺ»е№ҙеҸ—ж•ҷиӮІйғЁзӣёе…ійғЁй—Ёе§”жүҳпјҢеҸӮдёҺиө·иҚүе·ҘзЁӢзұ»зЎ•еЈ«д»Ҙе®һи·өжҲҗжһңз”іиҜ·еӯҰдҪҚзҡ„е…·дҪ“ж–№жЎҲпјҢвҖңеӨ©жҙҘеӨ§еӯҰж—©е°ұеңЁдёәжӯӨеҒҡеҮҶеӨҮдәҶ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иҝҷжҳҜдёҖеңәйқҷж°ҙжөҒж·ұзҡ„з ҙеҶ°д№ӢдёҫпјҢиҖҢж•Із ҙеҶ°еұӮзҡ„第дёҖжҠҠй•җеӨҙжҳҜеӯҰдҪҚжі•гҖӮеӯҰдҪҚ法第еҚҒе…«жқЎжҳҺзЎ®пјҢвҖңйҖҡиҝҮеӯҰдҪҚи®әж–Үзӯ”иҫ©жҲ–иҖ…规е®ҡзҡ„е®һи·өжҲҗжһңзӯ”иҫ©вҖқеқҮеҸҜиҺ·еҫ—еӯҰдҪҚгҖӮеҺ»е№ҙпјҢж•ҷиӮІйғЁжҢҮеҜје·ҘзЁӢдё“дёҡеӯҰдҪҚз ”з©¶з”ҹж•ҷиӮІжҢҮеҜје§”е‘ҳдјҡеҮәеҸ°зҡ„гҖҠе·ҘзЁӢзұ»еҚҡеЈ«дё“дёҡеӯҰдҪҚз ”з©¶з”ҹеӯҰдҪҚи®әж–ҮдёҺз”іиҜ·еӯҰдҪҚе®һи·өжҲҗжһңеҹәжң¬иҰҒжұӮпјҲиҜ•иЎҢпјүгҖӢпјҢд№ҹдёәе®һи·өжҲҗжһңеҲ’е®ҡдәҶжҳҺзЎ®иҫ№з•ҢпјҡвҖңе®һи·өжҲҗжһңеә”йқўеҗ‘еӣҪ家гҖҒиЎҢдёҡе’ҢеҢәеҹҹеҸ‘еұ•йңҖжұӮпјҢеӣҙз»•е®һйҷ…е·ҘзЁӢй—®йўҳпјҢдёҺйҮҚеӨ§е·ҘзЁӢе…ій”®жҠҖжңҜзӘҒз ҙгҖҒе®һзҺ°дјҒдёҡжҠҖжңҜиҝӣжӯҘе’ҢжҺЁеҠЁдә§дёҡеҚҮзә§зҙ§еҜҶз»“еҗҲгҖӮвҖқ
гҖҖгҖҖд»Һжі•еҫӢжқЎж–ҮеҲ°йғЁй—Ёи§„з« пјҢжҳҜз ҙеҶ°зҡ„ж №еҹәд№ҹжҳҜиө·зӮ№гҖӮ
гҖҖгҖҖеҢ—дә¬иҲӘз©әиҲӘеӨ©еӨ§еӯҰзӯүдё“йЎ№иҜ•зӮ№еҚ•дҪҚзҺҮе…ҲеҲ¶е®ҡзӣёе…іе®һж–Ҫз»ҶеҲҷпјҢжҳҺзЎ®дәҶе®һи·өжҲҗжһңзҡ„еӨҡз§ҚеҪўејҸе’Ңи®Өе®ҡж ҮеҮҶпјӣеұұдёңеӨ§еӯҰеҲӣи®ҫеӯҰдҪҚи®әж–ҮдёҺе®һи·өжҲҗжһңвҖңеҸҢиҪҰйҒ“вҖқжЁЎејҸпјӣиҘҝеҢ—е·ҘдёҡеӨ§еӯҰе°Ҷе®һи·өжҲҗжһңзәіе…ҘеӯҰжңҜз§ҜеҲҶиөӢеҲҶйЎ№зӣ®пјӣдёӯеӣҪзҹіжІ№еӨ§еӯҰз ”еҲ¶е®һи·өжҲҗжһңе…ЁжөҒзЁӢжҢҮеҜјжҖ§жЁЎжқҝпјӣйҮҚеәҶеӨ§еӯҰи®ҫз«ӢвҖңе®һи·өжҲҗжһңиҙЁйҮҸиҜ„е®ҡ委е‘ҳдјҡвҖқпјӣеҚҺеҚ—зҗҶе·ҘеӨ§еӯҰеҲӣж–°дјҒдёҡзҺ°еңәзӯ”иҫ©ж–№ејҸпјӣе“Ҳе°”ж»Ёе·ҘдёҡеӨ§еӯҰе»әз«ӢдәҶд»ҘеҲӣж–°д»·еҖјдёәеҜјеҗ‘зҡ„иҜ„д»·дҪ“зі»гҖӮ
гҖҖгҖҖж•ҷиӮІйғЁжҸҗдҫӣзҡ„ж•°жҚ®жҳҫзӨәпјҢ67д»Ҫе®һи·өжҲҗжһңдёӯе…ұжңү5з§ҚеҪўејҸпјҢе…¶дёӯж–№жЎҲи®ҫи®Ў31дёӘгҖҒдә§е“Ғи®ҫи®Ў20дёӘгҖҒи°ғз ”жҠҘе‘Ҡ2дёӘгҖҒжЎҲдҫӢеҲҶжһҗжҠҘе‘Ҡ2дёӘпјҢе…¶д»–еҪўејҸ12дёӘгҖӮжӯӨеӨ–пјҢиҝҷдәӣе®һи·өжҲҗжһңе…ұж¶үеҸҠ7дёӘдё“дёҡеӯҰдҪҚзұ»еҲ«пјҢз”өеӯҗдҝЎжҒҜзұ»еҚ жҖ»ж•°50.7%гҖӮ
гҖҖгҖҖе®ғ们йңҖжү“з ҙй•ҝжңҹеӣәеҢ–зҡ„еӯҰжңҜиҜ„д»·дҪ“зі»пјҢжһ„е»әе…Ёж–°зҡ„иҙЁйҮҸдҝқйҡңжңәеҲ¶пјҢжҜҸдёҖжӯҘйғҪж„Ҹе‘ізқҖеҜ№еҺҹжңүеҹ№е…»йҖ»иҫ‘зҡ„йў иҰҶдёҺйҮҚжһ„гҖӮжӯЈеҰӮеҢ—дә¬иҲӘз©әиҲӘеӨ©еӨ§еӯҰеӣҪ家еҚ“и¶Ҡе·ҘзЁӢеёҲеӯҰйҷўеёёеҠЎеүҜйҷўй•ҝжӣ№еәҶеҚҺжүҖиҜҙзҡ„йӮЈж ·пјҢвҖңд»Ҙе®һи·өжҲҗжһңжҺҲдәҲеӯҰдҪҚиҝҷжқЎи·Ҝд»ҺжқҘжІЎдәәиө°иҝҮпјҢиө°дёҠеҺ»жҳҜеҶ’йЈҺйҷ©зҡ„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еҮҝејҖи§Ӯеҝөзҡ„еҶ°еұӮ
гҖҖгҖҖжӣҙж·ұеұӮзҡ„жҢ‘жҲҳпјҢжҳҜеҮҝејҖи§Ӯеҝөзҡ„еҶ°еұӮгҖӮжӯӨеүҚпјҢж•ҷиӮІйғЁз ”究з”ҹеҸёжҢҮеҜјж•ҷиӮІйғЁеӯҰдҪҚдёҺз ”з©¶з”ҹж•ҷиӮІеҸ‘еұ•дёӯеҝғиҒҡз„ҰвҖңдё“дёҡеӯҰдҪҚз ”з©¶з”ҹд»Ҙе®һи·өжҲҗжһңз”іиҜ·еӯҰдҪҚиҗҪе®һжғ…еҶөвҖқејҖеұ•дё“йўҳи°ғз ”гҖӮз»“жһңжҸӯзӨәпјҢе°Ҫз®Ў79.27%зҡ„ж ЎеҶ…еҜјеёҲе’Ң91.46%зҡ„иЎҢдёҡеҜјеёҲи®Өдёәе®һи·өжҲҗжһңжӣҙиҙҙиҝ‘е®һйҷ…пјҢдҪҶдёӯдҪҺе№ҙзә§еӯҰз”ҹдёӯпјҢд»…33%иЎЁзӨәж„ҝж„Ҹе°қиҜ•гҖӮ
гҖҖгҖҖиҝҷз§Қи®ӨзҹҘе·®жәҗдәҺй•ҝжңҹвҖңе”Ҝи®әж–ҮвҖқиҜ„д»·еЎ‘йҖ зҡ„и·Ҝеҫ„дҫқиө–пјҢеӯҰз”ҹжӢ…еҝғе®һи·өжҲҗжһңиҙ№еҠӣдёҚи®ЁеҘҪпјҢеҜјеёҲеҝ§иҷ‘иҜ„д»·ж ҮеҮҶжЁЎзіҠгҖӮдёҖеҗҚжҜ•дёҡз”ҹеңЁжҺҘеҸ—дё“йўҳи°ғз ”и®ҝи°Ҳж—¶еқҰиЁҖпјҢвҖңиҝҷдёҖйҖүжӢ©жӣҙе…·жҢ‘жҲҳжҖ§пјҢе®һи·өжҲҗжһңйңҖиҰҒж №жҚ®дјҒдёҡе®һйҷ…й—®йўҳжҸҗеҮәеҸҜиҗҪең°зҡ„и§ЈеҶіж–№жЎҲпјҢ并д»Ҙе®һзү©еҪўејҸе‘ҲзҺ°пјҢжҜ”дёҖдәӣзәёдёҠи°Ҳе…өзҡ„еӯҰдҪҚи®әж–ҮйҡҫеәҰжӣҙеӨ§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вҖңеҫҲеӨҡеӯҰз”ҹеҜ№иҝҷжқЎи·Ҝд№ҹжңүз–‘иҷ‘пјҢдёҚж•ўиҪ»жҳ“е°қиҜ•гҖӮвҖқжӣ№еәҶеҚҺд№ҹеҗ‘дёӯйқ’жҠҘВ·дёӯйқ’зҪ‘и®°иҖ…дёҖдёҖеҲ—дёҫз ҙеҶ°зҡ„йҡҫзӮ№пјҢд»ҺеҜјеёҲе’ҢеӯҰз”ҹи§Ӯеҝөзҡ„иҪ¬еҸҳпјҢеҲ°е®һи·өжҲҗжһңзҡ„и®ӨеҸҜеәҰпјҢвҖңжңҖеҗҺпјҢе®һи·өжҲҗжһңжң¬иә«иҰҒиғҪжӢҝеҫ—еҮәжүӢпјҢеҰӮжҠҖжңҜжҠҘе‘ҠйңҖдјҒдёҡдёҘж јиҜ„е®ЎеҪ’жЎЈпјҢдё“еҲ©йңҖжҺҲжқғпјҢж ҮеҮҶйңҖеҸ‘еёғзҠ¶жҖҒжҲ–иЈ…еӨҮе·Ідә§з”ҹд»·еҖј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д»–з”ЁдёҖеҸҘиҜқжҖ»з»“пјҢиҝҷжҳҜдёӯеӣҪе·ҘзЁӢж•ҷиӮІд»ҺвҖңи®әж–ҮеҜјеҗ‘вҖқеҗ‘вҖңе®һи·өжң¬дҪҚвҖқзҡ„еҺҶеҸІжҖ§иҪ¬иә«пјҢжңҖз»ҲиҰҒвҖңеҹ№е…»зңҹжӯЈиғҪжңҚеҠЎеӣҪ家гҖҒе…·еӨҮе·ҘзЁӢеҲӣж–°иғҪеҠӣзҡ„дәәжүҚ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вҖңеӯҰз”ҹжғіз”Ёе®һи·өжҲҗжһңжӢҝеҲ°еӯҰдҪҚпјҢе°ұеҫ—иҜҒжҳҺдҪ зҡ„жҲҗжһңеҜ№еӣҪ家жҳҜжңүз”Ёзҡ„пјҢеҜ№еҸ‘еұ•жҳҜжңүз”Ёзҡ„гҖӮвҖқжӣ№еәҶеҚҺиҜҙгҖӮ
гҖҖгҖҖеңЁиҝҷж ·зҡ„иғҢжҷҜдёӢпјҢйҖүжӢ©жӢҝеҮәе®һи·өжҲҗжһңзҡ„еӯҰз”ҹпјҢйғҪеёҰдәҶдёҖзӮ№ж‘ёзқҖзҹіеӨҙиҝҮжІізҡ„еӯӨеӢҮгҖӮ
гҖҖгҖҖйҮҚеәҶеӨ§еӯҰзҡ„е·ҘзЁӢзЎ•еЈ«и‘ЈйңҮеңЁи®әж–Үе’Ңе®һи·өжҲҗжһңеҪ“дёӯиҝӣиЎҢжҠүжӢ©пјҢжңҖз»ҲйҖүдәҶеӮЁиғҪзі»з»ҹи®ҫи®ЎгҖӮвҖңжңүдёҖе®ҡдёҚзЎ®е®ҡжҖ§пјҢвҖқд»–еҜ№дёӯйқ’жҠҘВ·дёӯйқ’зҪ‘и®°иҖ…еқҰиЁҖпјҢвҖңдҪҶж №жҚ®еӯҰж ЎжҸҗдҫӣзҡ„е·ҘзЁӢзЎ•еЈ«жҜ•дёҡиҰҒжұӮзҡ„ж–Ү件пјҢжҲ‘ж„ҹи§үиҮӘиә«жқҗж–ҷз¬ҰеҗҲиҰҒжұӮ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дҪҶзңҹжӯЈи®©д»–дёӢе®ҡеҶіеҝғзҡ„пјҢжҳҜд»–еҸ‘зҺ°жӯЈеңЁеҮҶеӨҮдёӯзҡ„и®әж–ҮпјҢж— и®әеҰӮдҪ•йғҪж— жі•е®Ңж•ҙе‘ҲзҺ°иҮӘе·ұдёҖзӣҙд»ҘжқҘиҝӣиЎҢзҡ„е·ҘзЁӢе®һи·өеҶ…е®№гҖӮ
гҖҖгҖҖвҖңж”№з”Ёе®һи·өжҲҗжһңеҪўејҸеұ•зҺ°ж•ҲжһңжӣҙеҘҪгҖӮвҖқд»–жҖ»з»“гҖӮ
гҖҖгҖҖеҚҺеҚ—зҗҶе·ҘеӨ§еӯҰзҡ„е·ҘзЁӢзЎ•еЈ«еҲҳжқ°зҡ„з»ҸеҺҶжӣҙеҠ жӣІжҠҳпјҢд»–е·Із»ҸжҢүз…§еӯҰдҪҚи®әж–Үзҡ„иҰҒжұӮе®ҢжҲҗдәҶи®әж–ҮпјҢд№ҹз»ҷеҜјеёҲзңӢиҝҮпјҢвҖңиҫҫеҲ°дәҶзЎ•еЈ«жҜ•дёҡзҡ„иҰҒжұӮ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дҪҶд»–жңҖз»ҲиҝҳжҳҜеҶіе®ҡпјҢд»Ҙе®һи·өжҲҗжһңзҡ„еҪўејҸз”іиҜ·еӯҰдҪҚгҖӮиҝҷ件дәӢвҖңжІЎжңүе…ҲдҫӢвҖқпјҢи®©д»–йҡҫе…ҚеҝғйҮҢжІЎеә•гҖӮд»–еңЁзҪ‘дёҠжҹҘдәҶеҫҲд№…зҡ„жЎҲдҫӢпјҢжүҚжҹҘеҲ°е“Ҳе°”ж»Ёе·ҘдёҡеӨ§еӯҰжҹҗдҪҚеӯҰз”ҹзҡ„е®һи·өжҲҗжһңз”іиҜ·и®°еҪ•гҖӮ
гҖҖгҖҖвҖңе®һи·өжҲҗжһңеҜ№еңЁдјҒдёҡе®һи·өзҡ„еӯҰз”ҹжӣҙжңүеҲ©пјҢжӣҙе…іжіЁе·ҘзЁӢд»·еҖјиҖҢйқһзҗҶи®әеҲӣж–°гҖӮвҖқеҰӮд»Ҡе·Із»ҸжӢҝеҲ°дәҶеӯҰдҪҚиҜҒпјҢеҲҳжқ°дёҖиҫ№еӣһйЎҫжқҘж—¶и·ҜдёҖиҫ№ж„ҹж…ЁгҖӮ
гҖҖгҖҖиҝҷдёӘе№ҙиҪ»дәәеҪ“ж—¶иҝҳдёҚзҹҘйҒ“пјҢд»–е’ҢиҮӘе·ұжҹҘеҲ°зҡ„йӮЈдҪҚе“Ҳе·ҘеӨ§еӯҰз”ҹдёҖж ·пјҢйғҪжҳҜд»Ҡе№ҙд»Ҙе®һи·өжҲҗжһңиҺ·еҸ–еӯҰдҪҚиҜҒзҡ„дё“йЎ№иҜ•зӮ№е·ҘзЁӢзЎ•еЈ«д№ӢдёҖпјҢ他们жҳҜеқҗеңЁеҗҢдёҖеј жЎҢдёҠвҖңеҗғиһғиҹ№вҖқзҡ„67дәәд№ӢдёҖгҖӮ
гҖҖгҖҖеј зҷҫе·қд№ҹжҳҜвҖңеҗғиһғиҹ№вҖқзҡ„дёҖеҲҶеӯҗпјҢзӣ®еүҚе·ІжҲҗдёәиҒ”еҗҲеҹ№е…»дјҒдёҡзҡ„дёҖеҗҚжӯЈејҸе‘ҳе·ҘгҖӮеңЁд»–зңӢжқҘпјҢзңҹжӯЈзҡ„иҖғйӘҢеңЁе·ҘзЁӢзҺ°еңәгҖӮ
гҖҖгҖҖеј зҷҫе·қзҡ„е®һи·өжҲҗжһңпјҢжҳҜз”Ёе®һжҲҳдёӯж•°дёҚжё…зҡ„еӨұиҙҘе Ҷиө·жқҘзҡ„гҖӮдёәеҗҲжҲҗзҗҶжғіж ‘и„ӮпјҢд»–и·ҹзқҖеӣўйҳҹз»ҸеҺҶдәҶеӨ§еҚҠе№ҙвҖңеҗҲжҲҗ-иҜ„д»·-еӨұиҙҘ-еҶҚеҗҲжҲҗвҖқзҡ„еҫӘзҺҜпјҢиҮід»Ҡи®°еҫ—иҝһз»ӯ30ж¬Ўе®һйӘҢж•°жҚ®ејӮеёёзҡ„йӮЈдәӣеӨңжҷҡгҖӮеңЁеҫ·е·һзҡ„иҪҰй—ҙйҮҢпјҢиҝһз»ӯ40еӨ©зҡ„е®һйӘҢпјҢй»ҸеәҰеӨұжҺ§гҖҒеҺҹж–ҷжә¶и§Јзӯүй—®йўҳжҺҘиёөиҖҢиҮігҖӮдә§е“Ғз»ҲдәҺиҫҫж Үж—¶пјҢиҪҰй—ҙйҮҢзҲҶеҸ‘зҡ„ж¬ўе‘јеЈ°вҖңи®©жҲ‘зғӯжіӘзӣҲзң¶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вҖңиҝҷз§ҚвҖҳзңҹеҲҖзңҹжһӘвҖҷзҡ„е®һжҲҳзҺҜеўғпјҢжҳҜд№Ұжң¬е’Ңе®һйӘҢе®Өж— жі•жҜ”жӢҹзҡ„гҖӮвҖқд»–еҝҚдёҚдҪҸж„ҹж…ЁпјҢвҖңжҠҠи®әж–ҮеҸҳжҲҗдә§е“Ғзҡ„и·ҜпјҢжҳҜз”Ёжұ—ж°ҙдёҺеқҡжҢҒй“әе°ұзҡ„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д»Ҙе®һи·өжҲҗжһңдёәе·ҘзЁӢж•ҷиӮІз ҙеҶ°
гҖҖгҖҖеј зҷҫе·қеҗғдёҠдәҶвҖңиһғиҹ№вҖқпјҢеё®д»–зЁізЁіеҪ“еҪ“еқҗеңЁиҝҷеј жЎҢеӯҗеүҚзҡ„пјҢжҳҜдёӨе№ҙжқҘ4жң¬жІүз”ёз”ёзҡ„жүӢиҙҰпјҢ10дёҮдҪҷеӯ—зҝ”е®һи®°еҪ•дәҶжҜҸдёҖж¬Ўе®һйӘҢеҸӮж•°гҖҒеӨұиҙҘж•ҷи®ӯе’ҢжҖқз»ҙзў°ж’һзҡ„зҒ«иҠұгҖӮ
гҖҖгҖҖвҖңжҲ‘и®Өдёәд»Ҙе®һи·өжҲҗжһңз”іиҜ·еӯҰдҪҚпјҢе®ғзҡ„иҰҒжұӮе’ҢйҡҫеәҰжӣҙй«ҳдәҺеӯҰдҪҚи®әж–ҮпјҢжӣҙйҖӮз”ЁдәҺж ЎдјҒиҒ”еҗҲдәәжүҚеҹ№е…»пјҢжӣҙиғҪдҪ“зҺ°з”іиҜ·иҖ…зҡ„еә”з”ЁеҲӣж–°иғҪеҠӣпјҢд№ҹжӣҙз¬ҰеҗҲдё“дёҡеӯҰдҪҚз ”з©¶з”ҹж•ҷиӮІзҡ„еҹ№е…»зӣ®ж ҮпјҢдёҺиЎҢдёҡдјҒдёҡе®һйҷ…зҡ„дәәжүҚйңҖжұӮжӣҙеҠ йҖӮй…ҚгҖӮвҖқеј зҷҫе·қиҜҙгҖӮ
гҖҖгҖҖеҜ№жӯӨпјҢеҲҳеәҶеІӯзҡ„зңӢжі•жҳҜпјҢе®һи·өжҲҗжһңжҳҜйҒ“йҖүжӢ©йўҳпјҢеҸҜд»ҘйҖүи®әж–ҮпјҢд№ҹеҸҜд»ҘйҖүе®һи·өжҲҗжһңпјҢдҪҶзӣ®еүҚ并дёҚжҳҜжүҖжңүеӯҰж ЎгҖҒжүҖжңүе·ҘзЁӢзЎ•еҚҡеЈ«пјҢйғҪйҖӮеҗҲйҖүжӢ©еҗҺиҖ…гҖӮ
гҖҖгҖҖвҖңеӨ©жҙҘеӨ§еӯҰз”ұдәҺеҺҶеҸІз§ҜзҙҜиҫғеҘҪпјҢдёҺдјҒдёҡеҗҲдҪңеҹәзЎҖжүҺе®һпјҢеӣ жӯӨжҜ”иҫғжңүдҝЎеҝғгҖӮдҪҶеҜ№дәҺе…¶д»–еӯҰж ЎпјҢеҸҜиғҪдёҚе…·еӨҮиҝҷж ·зҡ„жқЎд»¶пјҢйңҖиҰҒж №жҚ®е®һйҷ…жғ…еҶөжқҘе®ҡгҖӮвҖқд»–иҜҙгҖӮ
гҖҖгҖҖеҚҠе№ҙжқҘпјҢеҲҳеәҶеІӯеңЁи®ёеӨҡй«ҳж ЎиҝӣиЎҢиҝҮе®Ји®ІпјҢеҮ зҷҫдёӘеӯҰж Ўзҡ„иҙҹиҙЈдәәеқҗеңЁеҸ°дёӢзңӢзқҖд»–гҖӮеҲҳеәҶеІӯжҳҺзҷҪпјҢеҪ“дёӯи®ёеӨҡй«ҳж Ўзҡ„иҖҒеёҲ并дёҚжҳҜйӮЈд№Ҳе®№жҳ“иғҪжӢҝеҲ°йЎ№зӣ®гҖӮ
гҖҖгҖҖвҖңиҝҷз§Қжғ…еҶөдёӢиҝҳиҰҒвҖҳйҖјвҖҷеӯҰз”ҹжӢҝеҮәе®һи·өжҲҗжһңпјҢеҸҜиғҪе°ұдёҚеӨӘзҺ°е®һгҖӮвҖқд»–дёҖй’Ҳи§ҒиЎҖең°иҜҙгҖӮ
гҖҖгҖҖд»Ҙе®һи·өжҲҗжһңдёәе·ҘзЁӢж•ҷиӮІз ҙеҶ°пјҢе°‘дёҚдәҶйЎ№зӣ®зҡ„зүөеј•гҖӮеҲҳеәҶеІӯи®ӨдёәпјҢиҝҷе°Ҷйј“еҠұзӣёе…ій«ҳж ЎзңҹжӯЈжҠҠе·ҘзЁӢж•ҷиӮІзҡ„з«Ӣи¶ізӮ№ж”ҫеҲ°вҖңдёәеӣҪ家з»ҸжөҺе’ҢдјҒдёҡи§ЈеҶіе®һйҷ…й—®йўҳвҖқдёҠпјҢиҖҢдёҚжҳҜжҠҠеӯҰз”ҹе…іеңЁиұЎзүҷеЎ”йҮҢеҶҷи®әж–ҮгҖӮ
гҖҖгҖҖвҖңиҝҷз§ҚеҜјеҗ‘йј“еҠұдәәжүҚеҹ№е…»дёӢеҹәеұӮпјҢжҠ“зңҹй—®йўҳпјҢжңүеҠ©дәҺдҝғиҝӣеӣҪ家зҡ„еҸ‘еұ•гҖӮвҖқд»–е»әи®®пјҢзӣёе…ійҷўж ЎеҸҜд»Ҙе’Ңең°ж–№дјҒдёҡиҒ”еҠЁпјҢд»Һе°ҸйЎ№зӣ®ејҖе§Ӣз§ҜзҙҜз»ҸйӘҢгҖӮвҖңеҸӘиҰҒиӮҜдёҺдјҒдёҡеҜ№жҺҘпјҢжҖ»иғҪжүҫеҲ°еҗҲдҪңжңәдјҡгҖӮвҖқ
гҖҖгҖҖеҲҳеәҶеІӯж„ҹж…Ёең°жҸҗеҲ°пјҢеҪ“еүҚпјҢи®ёеӨҡз§‘з ”еһӢдјҒдёҡзҡ„з ”еҸ‘иғҪеҠӣе’Ңж°ҙе№іпјҢз”ҡиҮівҖңе·Із»Ҹи¶…иҝҮй«ҳж ЎвҖқпјҢеҰӮжһңдёҚе°Ҫж—©дёҺиҝҷдәӣйҫҷеӨҙдјҒдёҡеҜ№жҺҘпјҢй«ҳж ЎеҸҜиғҪдјҡиў«з”©еңЁеҗҺиҫ№гҖӮжӯӨеӨ–пјҢеҰӮжһңеӯҰз”ҹиғҪеңЁиҜ»зЎ•еЈ«жңҹй—ҙе°ұдёҺдјҒдёҡеҜҶеҲҮжҺҘи§ҰпјҢвҖңе°ұдёҡдјҡжӣҙе®№жҳ“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жңӘжқҘзҡ„е®һи·өиҝҳйңҖйӘҢиҜҒгҖӮзңјдёӢзҡ„67д»Ҫе·ҘзЁӢе®һи·өжҲҗжһңпјҢеҲҷжҳҜе·Із»Ҹе°ҶеҲӣж–°зӘҒз ҙзҡ„жҲҳеңәд»Һзәёйқўи®әж–ҮиҪ¬еҗ‘иҪҰй—ҙе·Ҙең°пјҢиҜҒжҳҺдәҶеҰӮжһңжі•еҫӢиөӢжқғгҖҒж”ҝзӯ–й…ҚеҘ—дёҺй«ҳж Ўж”№йқ©иғҪеҪўжҲҗеҗҲеҠӣпјҢе°ұиғҪдёәе·ҘзЁӢдәәжүҚејҖиҫҹеҮәдёҖжқЎд»Ҙе®һжҲҳиғҪеҠӣдёәж ёеҝғзҡ„иҜ„д»·йҖҡйҒ“гҖӮ
гҖҖгҖҖеңЁдё“йўҳи°ғз ”дёӯд№ҹжҸҗеҲ°пјҢй«ҳж ЎйўҶеҜје’Ңзӣёе…із®ЎзҗҶйғЁй—Ёжҷ®йҒҚи®ӨдёәпјҢе®һи·өжҲҗжһңжҳҜдё“дёҡеӯҰдҪҚдәәжүҚеҹ№е…»жЁЎејҸж”№йқ©зҡ„йҮҚиҰҒеҲҮе…ҘеҸЈпјҢвҖңзӘҒз ҙдәҶд»ҘеӯҰдҪҚи®әж–Үз”іиҜ·еӯҰдҪҚзҡ„е”ҜдёҖж ҮеҮҶпјҢж Үеҝ—зқҖиҜ„д»·ж ҮеҮҶеҗ‘еә”з”Ёд»·еҖјеҜјеҗ‘иҪ¬еҸҳвҖқпјҢвҖңи®©еӯҰз”ҹеңЁзңҹе®һзҡ„е·ҘзЁӢе’Ңе·ҘдҪңеңәжҷҜдёӯе®ҢжҲҗеӯҰжңҜи®ӯз»ғпјҢд№ҹйҖјзқҖеӯҰж ЎеҸҚжҖқе’ҢйҮҚжһ„дё“дёҡеӯҰдҪҚеҹ№е…»жЁЎејҸвҖқгҖӮ
гҖҖгҖҖвҖңж–°дёҖиҪ®з§‘жҠҖйқ©е‘Ҫе’Ңдә§дёҡеҸҳйқ©еҠ йҖҹжј”иҝӣпјҢеҠ еҝ«еҹ№иӮІж–°иҙЁз”ҹдә§еҠӣпјҢеҜ№е·ҘзЁӢдәәжүҚзҡ„еҹ№е…»и§„ж јгҖҒеұӮж¬Ўе’ҢиҙЁйҮҸжҸҗеҮәж–°зҡ„жӣҙй«ҳиҰҒжұӮпјҢеҝ…йЎ»жҺўзҙўеҪўжҲҗжӣҙеҠ з¬ҰеҗҲж•ҷиӮІи§„еҫӢгҖҒжӣҙеҠ з¬ҰеҗҲдәәжүҚжҲҗй•ҝ规еҫӢзҡ„еҹ№е…»ж ҮеҮҶпјҢд»ҘиҜ„д»·ж”№йқ©дёәзүөеј•жҺЁеҠЁеҹ№е…»жЁЎејҸзҡ„иҝӯд»ЈеҚҮзә§гҖӮвҖқж•ҷиӮІйғЁз ”究з”ҹеҸёжңүе…іиҙҹиҙЈдәәиҜҙгҖӮ
гҖҖгҖҖдёӯйқ’жҠҘВ·дёӯйқ’зҪ‘и®°иҖ… еј жёә





 дә¬е…¬зҪ‘е®үеӨҮ 11010102004843еҸ·
дә¬е…¬зҪ‘е®үеӨҮ 11010102004843е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