ه¼؛ه›½é’ه¹´ç§‘ه¦ه®¶ï¼ڑé،¶ه¤©ن¹ںè¦پç«‹هœ°
هڈ‘ç¨؟و—¶é—´ï¼ڑ2025-10-31 10:20:00 و¥و؛گï¼ڑ ن¸ه›½é’ه¹´و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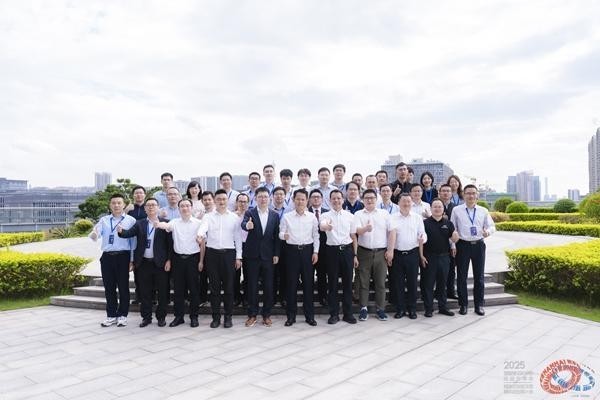
م€€م€€2025ه¼؛ه›½é’ه¹´ç§‘ه¦ه®¶و´»هٹ¨هˆ†ن؛«ن¼ڑهڈ‚ن¼ڑهک‰ه®¾هگˆه½±م€‚وœ¬ç‰ˆه›¾ç‰‡ه‡ç”±ن¸»هٹو–¹وڈگن¾›
م€€م€€ç¼–者وŒ‰
م€€م€€ن؛”è½½ه…‰éک´ï¼Œو¥ه±¥é“؟锵م€‚è‡ھ“هچپه››ن؛”â€ه¼€ه±€ن¹‹ه¹´هگ¯èˆھçڑ„“ه¼؛ه›½é’ه¹´ç§‘ه¦ه®¶â€è¯„选,هœ¨ه¹´è½»çڑ„科ه¦ه·¥ن½œè€…ن¹‹ن¸ه·²ç»ڈو؟€èµ·ن؛†ه±‚ه±‚و¶ںو¼ھم€‚ن؛”ه±ٹç››ن¼ڑ,ن¸چن»…وک¯ن¸€ç³»هˆ—èچ£èھ‰çڑ„é¢پهڈ‘,و›´وک¯ن¸€ه؛§ç²¾ه؟ƒو„ç‘çڑ„“立ن؛¤و،¥â€ï¼ڑه®ƒè®©هœ°و–¹هڈ‘ه±•çڑ„è؟«هˆ‡éœ€و±‚م€پن¼پن¸ڑ转ه‹çڑ„و¾ژو¹ƒهٹ¨èƒ½ن¸ژé’ه¹´ç§‘ه¦ه®¶çڑ„ه¥‡و€ه¦™وƒ³هœ¨و¤ن؛¤و±‡م€پ碰و’م€پèچهگˆم€‚ن¸ه›½é’ه¹´وٹ¥ç¤¾ن½œن¸؛“科وٹ€ç؛¢ه¨کâ€5ه¹´çڑ„耕è€ک,ه·²ç»“ه‡؛ن؛§ه¦ç ”و·±ه؛¦èچهگˆçڑ„ç،•وœم€‚
م€€م€€ç«™هœ¨â€œهچپن؛”ن؛”â€çڑ„é—¨و§›ن¸ٹ,وˆ‘ن»¬çœ؛وœ›çڑ„وک¯ن¸€ç‰‡و›´ه£®éک”ن¹ںو›´ه…·وŒ‘وˆکçڑ„ه›¾و™¯م€‚وˆ‘ن»¬è¦پهٹ ه¼؛هژںه§‹هˆ›و–°ه’Œه…³é”®و ¸ه؟ƒوٹ€وœ¯و”»ه…³ï¼›è¦په®Œه–„و–°ه‹ن¸¾ه›½ن½“هˆ¶ï¼Œé‡‡هڈ–超ه¸¸è§„وژھو–½ï¼Œه…¨é“¾و،وژ¨هٹ¨é›†وˆگ电路م€په·¥ن¸ڑو¯چوœ؛م€پé«ک端ن»ھه™¨م€پهں؛ç،€è½¯ن»¶م€په…ˆè؟›وگو–™م€پç”ں物هˆ¶é€ ç‰é‡چ点领هںںه…³é”®و ¸ه؟ƒوٹ€وœ¯و”»ه…³هڈ–ه¾—ه†³ه®ڑو€§çھپç ´م€‚و—¶ن»£çڑ„èپڑه…‰çپ¯ï¼Œو¯”ن»¥ه¾€ن»»ن½•و—¶ه€™éƒ½و›´هٹ èپڑ焦ن؛ژé’ه¹´ç§‘ه¦ه®¶ç¾¤ن½“م€‚ن»–ن»¬و€ç»´و´»è·ƒم€پç²¾هٹ›ه……و²›ï¼Œوœ€ه…·é¢ 覆و€§هˆ›و–°çڑ„ه‹‡و°”,çگ†ه؛”ن»ژ科وٹ€هˆ›و–°çڑ„“ç”ںهٹ›ه†›â€هٹ é€ںè؟ˆهگ‘“ن¸»هٹ›ه†›â€م€‚è؟™ن»½è´£ن»»ï¼Œé‡چè‹¥هچƒé’§م€‚
م€€م€€è؟™ن»½è´£ن»»ï¼Œوک¯â€œن»ژ1هˆ°Nâ€çڑ„ه¼€و‹“,و›´وک¯â€œن»ژ0هˆ°1â€çڑ„ه¼•é¢†م€‚و£ه¦‚ه¼؛ه›½é’ه¹´ç§‘ه¦ه®¶ن»¬ن»ٹه¹´çڑ„ç؛ھه؟µه“پ——“èژ«و¯”ن¹Œو–¯çژ¯â€é‚£ç¥ه¥‡çڑ„“و‰è½¬â€م€‚è¦پو‰“ç ´ه¸¸è§„çڑ„و€ç»´ه®ڑه¼ڈ——و—¢وœ‰ç§‘ه¦هœˆçڑ„,ن¹ںوœ‰ن¼پن¸ڑçڑ„م€پهœ°و–¹و”؟ه؛œçڑ„,و‰چ能هڈ‘çژ°ç»ںن¸€è€Œè؟ç»çڑ„و–°ن¸–ç•Œم€‚
م€€م€€è؟™ن»½è´£ن»»ï¼Œوک¯â€œç‹¬وœ¨وˆگو—â€çڑ„é’»ç ”ï¼Œو›´وک¯â€œن¸‡وœ¨ه…±ç”ںâ€çڑ„هچڈهگŒم€‚çژ°ن»£é‡چه¤§ç§‘ه¦é—®é¢کçڑ„çھپç ´ï¼Œو„ˆهڈ‘ن¾èµ–è·¨ه¦ç§‘م€پ跨领هںںçڑ„集ن½“هچڈن½œم€‚“هچپه››ن؛”â€وœںé—´وگه»؛çڑ„“碰و’ن¸ژèپ”هگˆâ€ه¹³هڈ°ï¼Œهœ¨â€œهچپن؛”ن؛”â€ه؛”هچ‡ç»´ن¸؛و›´و·±ه؛¦çڑ„“ه…±ç”ںâ€ç”ںو€پم€‚é’ه¹´ç§‘ه¦ه®¶ه؛”ن¸»هٹ¨و‹†é™¤ه¦ç§‘é—´çڑ„“篱笆ه¢™â€ï¼Œو—¢èƒ½هœ¨è‡ھه·±çڑ„ن¸“ن¸ڑ领هںںو·±è€•ن¸چè¾چ,ن¹ں能ن¸ژن¸چهگŒèƒŒو™¯çڑ„هگŒè،Œم€پن¼پن¸ڑه®¶م€په·¥ç¨‹ه¸ˆوگ؛و‰‹ï¼Œه½¢وˆگو”»ه…‹â€œهچ،è„–هگâ€éڑ¾é¢کçڑ„èپ”هگˆه›¢éکں,让و™؛و…§çڑ„碰و’ن؛§ç”ں“1+1>2â€çڑ„هŒ–ه¦هڈچه؛”م€‚
م€€م€€ه¤§و½®ه¥”و¶Œï¼Œهگژوµھو¾ژو¹ƒم€‚é’ه¹´ç§‘ه¦ه®¶ن»¬و‰‹وڈ،هژ†هڈ²çڑ„وژ¥هٹ›و£’,ه‰چو–¹وک¯ه»؛设科وٹ€ه¼؛ه›½çڑ„وکںè¾°ه¤§وµ·م€‚و„؟ن»–ن»¬هœ¨â€œهچپن؛”ن؛”â€çڑ„و–°ه¾پ程ن¸ٹ,ن»¥â€œه¼€è·¯ه…ˆé”‹â€çڑ„é”گو°”,ه°†هˆ›و–°çڑ„çپ«ç‚¬ç‡ƒه¾—و›´و—؛,هœ¨ن¸ه›½ه¼ڈçژ°ن»£هŒ–çڑ„ن¼ںه¤§ه®è·µن¸ï¼Œن¹¦ه†™ه±ن؛ژè‡ھه·±çڑ„çپ؟çƒ‚ç¯‡ç« ï¼Œو±‡ه…¥و°‘و—ڈه¤چه…´çڑ„ه£®ن¸½وکںو²³ï¼پ
م€€م€€â€”—————————
م€€م€€è؟™وک¯ن¸€ç¾¤ه¾ˆه°‘ه‡؛çژ°هœ¨èپڑه…‰çپ¯ن¸‹çڑ„é’ه¹´ç§‘ه¦ه®¶م€‚ه¤ڑو•°و—¶ه€™ï¼Œن»–ن»¬و•£ه¸ƒهœ¨ه…¨ه›½هگ„هœ°çڑ„é«کو ،م€پن¼پن¸ڑم€پهŒ»é™¢م€په®éھŒه®¤ï¼Œوœ‰çڑ„هœ¨ç”°é—´هœ°ه¤´ï¼Œهں‹ه¤´ç§‘ç ”م€‚9وœˆ28و—¥ï¼Œè؟™ç¾¤é’ه¹´é½گèپڑه¹؟ن¸œن½›ه±±هچ—وµ·هŒ؛çڑ„ه£هچژه®éھŒه®¤ï¼Œç›¸ç»§èµ°هˆ°èپڑه…‰çپ¯ن¸‹م€‚
م€€م€€è؟™ن¸€ه¤©ï¼Œ2025ه¼؛ه›½é’ه¹´ç§‘ه¦ه®¶و´»هٹ¨هˆ†ن؛«ن¼ڑهœ¨ن½›ه±±ن¸¾è،Œï¼Œè®¸ه¤ڑ科ه¦ه®¶ه؟™é‡Œهپ·é—²ï¼Œèµ¶و¥هڈ‚هٹ م€‚ç»ڈن¸“ه®¶ه¤ڑè½®وژ¨èچگ,11ن½چ“ه¼؛ه›½é’ه¹´ç§‘ه¦ه®¶â€ه…¥é€‰è€…م€پ39ن½چوڈگهگچ者,ن»ژه…¨ه›½188ه®¶هچ•ن½چçڑ„è؟‘400هگچوژ¨èچگ者ن¸è„±é¢–而ه‡؛م€‚
م€€م€€è®¸ه¤ڑن؛؛ه¹´ç؛ھ轻轻——وœ€ه¹´è½»çڑ„35ه²پ,وœ€ه¹´é•؟者ن¹ںو‰چ40ه²پ,هچ´éƒ½وک¯و‰€هœ¨é¢†هںںçڑ„ن½¼ن½¼è€…م€‚
م€€م€€ه…¶ن¸ï¼Œوœ‰و›¾هœ¨و–°ه† ç–«وƒ…وœںé—´هˆ›ه»؛ن¼ وں“ç—…هٹ¨هٹ›ه¦و¨،ه‹çڑ„و°é’ï¼›وœ‰ن»ژن؛‹è،¨ç•Œé¢ç‰©çگ†هٹ›ه¦ç ”究çڑ„ه¥³و•™وژˆï¼›وœ‰هڈ‚ن¸ژن¸–界首ن¸ھçœںو ¸ç”ں物هں؛ه› 组هگˆوˆگè®،هˆ’çڑ„90هگژé’ه¹´ï¼›وœ‰و‰ژو ¹ن؛؛ه·¥و™؛能ن¸ژè‡ھهٹ¨é©¾é©¶é¢†هںںçڑ„ن¸“ه®¶ï¼›è؟کوœ‰è‡´هٹ›ن؛ژç²¾ç¥هŒ»ه¦ç ”究çڑ„ه›½ه®¶ç؛§é¢†ه†›ن؛؛و‰چ……

م€€م€€ن½›ه±±ه¸‚هچ—وµ·هŒ؛هŒ؛é•؟çژ‹ه‹‡ن¼ڑه‰چوژ¨ن»‹هچ—وµ·هŒ؛ن؛؛و‰چ科هˆ›هڈ‘ه±•çژ¯ه¢ƒم€‚
م€€م€€وژ¢و±‚وœھçں¥ è‡ھهٹ›و›´ç”ں
م€€م€€ç”ںن؛ژ1990ه¹´çڑ„ç½—ه‘¨هچ؟,وک¯2025ه¹´â€œه¼؛ه›½é’ه¹´ç§‘ه¦ه®¶â€ن¸وœ€ه¹´è½»çڑ„ه…¥é€‰è€…م€‚
م€€م€€ه¦‚ن»ٹ,35ه²پçڑ„ن»–ه·²وک¯هژ¦é—¨ه¤§ه¦ç”ںه‘½ç§‘ه¦ه¦é™¢و•™وژˆï¼Œن¸“و³¨ن؛ژهگˆوˆگç”ں物ه¦çڑ„ç ”ç©¶م€‚10ن½™ه¹´ه‰چ,هœ¨و¸…هچژه¤§ه¦è¯»ç ”و—¶ه›½ه†…ه¤–“هگˆوˆگç”ں物ه¦â€ه…´èµ·ï¼Œç½—ه‘¨هچ؟ن¾؟هڈ‚ن¸ژهˆ°ن؛†ن¸–界首ن¸ھçœںو ¸ç”ں物هں؛ه› 组هگˆوˆگè®،هˆ’م€‚
م€€م€€ه¯¹ç½—ه‘¨هچ؟而言,那وک¯ن¸€ن¸ھه……و»،وœھçں¥çڑ„ن¸–界,هˆ°ه¤„都وک¯â€œن»ژ0هˆ°1â€çڑ„ç ”ç©¶م€‚
م€€م€€هگˆوˆگç”ں物ه¦وک¯è؟‘ه¹´و¥هڈ‘ه±•è؟…猛çڑ„و–°ه…´ه‰چو²؟ن؛¤هڈ‰ه¦ç§‘,被认ن¸؛وک¯â€œç¬¬ن¸‰و¬،ç”ں物وٹ€وœ¯é©ه‘½â€م€‚ç½—ه‘¨هچ؟ه‘ٹ诉记者ï¼ڑ“هں؛ه› 组ن½œن¸؛ç”ںه‘½ن؟،وپ¯çڑ„è½½ن½“,能هگ¦ن؛؛ه·¥هگˆوˆگ,ه¹¶ç”¨ن؛ژو”¯وŒپç”ںه‘½هکو´»ï¼Œوک¯هگˆوˆگç”ںه‘½çڑ„ه…³é”®م€‚â€
م€€م€€هگژو¥ï¼Œن»–ن¸ژهگˆن½œè€…ن¸€هگŒو”»ه…‹ن؛†è¯¥é،¹ç›®çڑ„诸ه¤ڑéڑ¾é¢ک,وˆگهٹںو„ه»؛ن؛†ن¸–界首و،Mbç؛§çœںو ¸ç”ں物ç؛؟و€§هگˆوˆگوں“色ن½“,相ه…³ه¦وœ¯وˆگوœهœ¨م€ٹ科ه¦م€‹ï¼ˆScience)ç‰ه›½é™…é،¶ç؛§وœںهˆٹهڈ‘è،¨م€‚该وˆگوœه…¥é€‰â€œ2017ه¹´ه؛¦ن¸ه›½ç§‘ه¦هچپه¤§è؟›ه±•â€ï¼Œè؟™ن¹ںو ‡ه؟—ç€وˆ‘ه›½çœںو ¸ن؛؛ه·¥هں؛ه› 组هگˆوˆگç ”ç©¶و°´ه¹³è·»è؛«ن¸–ç•Œه‰چهˆ—م€‚
م€€م€€è؟™è®©ç½—ه‘¨هچ؟看هˆ°ن؛†هگˆوˆگç”ں物ه¦çڑ„é…هٹ›م€‚“ه¦‚هگŒé«کو‰‹è؟‡و‹›ï¼Œن½ è§پهˆ°ن؛†و›´هٹ هژ‰ه®³çڑ„é«کو‰‹م€‚â€ç½—ه‘¨هچ؟و‰“ن؛†ن¸ھو¯”و–¹ï¼ڑ“ه¦‚وœè¯´ن¼ ç»ںç”ں物ه¦وک¯â€کو‹†è§£و±½è½¦â€™ï¼Œهگˆوˆگç”ں物ه¦ه°±وک¯â€کهˆ¶é€ و±½è½¦â€™م€‚â€
م€€م€€â€œ1+1ï¼2çڑ„و¶Œçژ°و•ˆه؛”,وک¯è؟™é—¨ه¦ç§‘وœ€è؟·ن؛؛çڑ„هœ°و–¹م€‚â€ç½—ه‘¨هچ؟è،¨ç¤؛,ن»–ه–œو¬¢هœ¨وœھçں¥ن¸و‘¸ç´¢ï¼Œè؟™ن¸ھè؟‡ç¨‹ه……و»،وŒ‘وˆک,و—¶ه¸¸è®©ن»–و„ںهˆ°هˆ؛و؟€ه’Œه…´ه¥‹م€‚
م€€م€€هœ¨èژ·ه¾—“ه¼؛ه›½é’ه¹´ç§‘ه¦ه®¶â€ç§°هڈ·çڑ„11ن½چé’ه¹´ن¸ï¼Œè®¸ه¤ڑن؛؛都وک¯ن»ژوœھçں¥ن¸è¹ڑه‡؛è·¯و¥çڑ„م€‚
م€€م€€36ه²پçڑ„هچ—ن؛¬èˆھç©؛èˆھه¤©ه¤§ه¦و•™وژˆوژé›ھو¢…,وک¯ن»ٹه¹´ه”¯ن¸€ه…¥é€‰çڑ„ه¥³و€§ç§‘ه¦ه®¶م€‚è؟™ن¸ھوگو–™ç§‘ه¦ن¸ژوٹ€وœ¯ه¦é™¢çڑ„و•™وژˆï¼Œن¸ژه›¢éکںهڈ‘çژ°ه¹¶وڈگه‡؛çڑ„“و°´ن¼ڈو•ˆه؛”â€â€”—ن»ژو°´ن¸ç›´وژ¥èژ·هڈ–电能,而هگژé€ڑè؟‡و”»ه…³ه°†هڈ‘电و€§èƒ½وڈگهچ‡6ن¸ھé‡ڈç؛§ï¼Œوژ¨هٹ¨هں؛ç،€ç§‘ه¦هگ‘ه·¥ç¨‹وٹ€وœ¯çڑ„è·¨è¶ٹم€‚
م€€م€€â€œوˆ‘认ن¸؛科ه¦ه®¶ç²¾ç¥وœ€و ¸ه؟ƒçڑ„特质وک¯ï¼Œçں¢ه؟—ن¸چو¸çڑ„وژ¢ç´¢ç²¾ç¥م€‚â€وژé›ھو¢…说,è؟™èƒŒهگژهŒ…هگ«ن؛†ç”کهگه†·و؟ه‡³çڑ„è€گه؟ƒم€په‹‡é—¯و— ن؛؛هŒ؛çڑ„ه‹‡و°”,ن»¥هڈٹن¸€ن»½وœچهٹ،ه›½ه®¶م€پé€ ç¦ڈن؛؛و°‘çڑ„هˆه؟ƒم€‚
م€€م€€هگŒèژ·â€œه¼؛ه›½é’ه¹´ç§‘ه¦ه®¶â€ç§°هڈ·çڑ„37ه²پهŒ»ç”ںه‘¨و–°é›¨ï¼Œهœ¨è؟‡هژ»10ن½™ه¹´é‡Œï¼Œèپڑ焦ه„؟ç«¥é’ه°‘ه¹´وٹ‘éƒپç—‡è¯ٹç–—éڑ¾é¢کم€‚هœ¨é‡چه؛†هŒ»ç§‘ه¤§ه¦é™„ه±ç¬¬ن¸€هŒ»é™¢ï¼Œن»–ه¸¦é¢†ه›¢éکںه¼€ه±•ç³»ç»ںو”»ه…³ï¼Œé¦–و¬،هڈ‘çژ°ه„؟ç«¥é’ه°‘ه¹´وٹ‘éƒپç—‡و—©وœںç›وں¥è¯ٹو–و ‡ه؟—物,ه¹¶çژ‡ه…ˆوڈگه‡؛ه„؟ç«¥é’ه°‘ه¹´وٹ‘éƒپç—‡ه”¯ن¸€وژ¨èچگèچ¯ç‰©و²»ç–—و–°و–¹و،ˆï¼Œو”¹ه†™ç¾ژه›½ه’Œن¸ه›½èچ¯ç›‘部门用èچ¯وژ¨èچگم€‚
م€€م€€ه‘¨و–°é›¨ه‘ٹ诉记者,هœ¨هŒ»ه¦وٹ€وœ¯ن¸ٹ,ن»–ن¹ںو›¾éپ‡هˆ°ه›½ه¤–“هچ،è„–هگâ€çڑ„وƒ…ه†µم€‚
م€€م€€ن»–ه’Œه›¢éکںهœ¨هپڑه¾ھè¯پهŒ»ه¦ه®éھŒو—¶ï¼Œè¦پ用هˆ°ن¸€ç§چو•°وچ®هˆ†وگوٹ€وœ¯ï¼Œن½†è؟™ç§چوٹ€وœ¯هœ¨ه…¨çگƒèŒƒه›´ه†…هڈھوœ‰ه°‘و•°ه‡ ن¸ھهŒ»ه¦وœ؛و„وژŒوڈ،م€‚“وˆ‘ن»¬ه°è¯•è·ںن»–ن»¬هگˆن½œï¼Œن½†éƒ½è¢«و‹’ç»ï¼Œوˆ–说è¦پهگˆن½œهڈ¯ن»¥ï¼Œوˆگوœوک¯وˆ‘ن»¬çڑ„م€‚â€
م€€م€€â€œو ¸ه؟ƒوٹ€وœ¯وک¯ç‰ن¸چو¥م€پè¦پن¸چو¥çڑ„,è؟کوک¯è¦پè‡ھهٹ›و›´ç”ںم€‚â€ه‘¨و–°é›¨è¯´ï¼Œè€Œهگژن»–ن»¬ه†³ه®ڑ组ه»؛و”»هڑه°ڈ组,è؟›è،Œوٹ€وœ¯çھپç ´ï¼Œâ€œوˆ‘ن»¬è؟‡ه¹´éƒ½و²،وœ‰ه›ه®¶هگƒن½ڈ,都هœ¨ه®éھŒه®¤é‡Œâ€م€‚ن»–ن»¬èٹ±ن؛†ن¸€ه¹´و—¶é—´ï¼Œوœ€ç»ˆوژŒوڈ،و ¸ه؟ƒوٹ€وœ¯ï¼Œه¹¶هœ¨و¤هں؛ç،€ن¸ٹو„ه»؛起独ه±ن¸ه›½çڑ„ه„؟ç«¥é’ه°‘ه¹´وٹ‘éƒپç—‡ه¤§و•°وچ®و¨،ه‹م€‚
م€€م€€37ه²پçڑ„è¥؟ه®‰ن؛¤é€ڑه¤§ه¦وگو–™هŒ–ه·¥ç ”究و‰€و‰€é•؟ه”گن¼ں,2018ه¹´ه¦وˆگه½’ه›½هگژè؟…é€ں组ه»؛ç§‘ç ”ه›¢éکں,针ه¯¹èƒ½و؛گهڈٹ“هڈŒç¢³â€ه›½ه®¶é‡چه¤§éœ€و±‚,ن¸“و³¨ن؛ژé«ک能电هŒ–ه¦ç”µو± è؟™ن¸€â€œه†›و°‘ن¸¤è؟«هˆ‡â€çڑ„“هچ،è„–هگâ€é¢†هںں,çھپç ´ن؛†ه…³é”®و€§çڑ„é«کو€§èƒ½ç”µهŒ–ه¦ه‚¨èƒ½وگو–™و„و•ˆه…³ç³»è€¦هگˆéڑ¾é¢کم€‚
م€€م€€â€œé¢ه¯¹ن¼—ه¤ڑé«ک端装ه¤‡è¢«ه›½ه¤–وژŒوژ§çڑ„ه±€é¢ï¼Œه®çژ°وٹ€وœ¯è‡ھن¸»وک¯وˆ‘ن»¬ه؟…é،»è¦پو‰؟و‹…çڑ„ن½؟ه‘½م€‚â€هœ¨â€œه¼؛ه›½é’ه¹´ç§‘ه¦ه®¶â€ه”گن¼ں看و¥ï¼Œو”»ه…‹ه›؛و€پ电و± çڑ„装ه¤‡هˆ¶é€ وٹ€وœ¯ï¼Œه°†è‡ھن¸»çں¥è¯†ن؛§وƒç‰¢ç‰¢وژŒوڈ،هœ¨è‡ھه·±و‰‹ن¸ï¼Œو—¢وک¯è‡ھه·±çڑ„هڑه®ڑن؟،ه؟µï¼Œن¹ںوک¯ه›¢éکںن¸چو‡ˆه¥‹و–—çڑ„ç›®و ‡م€‚
م€€م€€â€œç§‘ç ”çڑ„وœھو¥éœ€è¦پâ€ک眼ç›â€™م€‚â€و¹–هچ—ه¤§ه¦وگو–™ç§‘ه¦ن¸ژه·¥ç¨‹ه¦é™¢و•™وژˆه¾گه…ˆن¸œè¯´ï¼Œن»–هڈ£ن¸çڑ„“眼ç›â€وŒ‡çڑ„وک¯ن¸‰ç»´هژںهگوژ¢é’ˆï¼Œè؟™وک¯ن؛؛ç±»وژ¢çں¥ç‰©è´¨ن¸–ç•Œçڑ„眼ç›ï¼Œوœ‰ن؛†ه®ƒï¼Œن؛؛ç±»و‰چ能çھپç ´ن؛Œç»´ه¹³é¢ï¼Œçœ‹هˆ°و›´ç«‹ن½“çڑ„ن¸‰ç»´هژںهگن¸–ç•Œم€‚
م€€م€€ç„¶è€Œï¼Œن¸‰ç»´هژںهگوژ¢é’ˆوک¯ç§‘ه¦ن»ھه™¨ç•Œهگچه‰¯ه…¶ه®çڑ„ه¥¢ن¾ˆه“پم€‚è؟‡هژ»ه‡ هچپه¹´ï¼Œç¾ژه›½هœ¨è؟™ç‰‡و±ںو¹–独هچ 鳌ه¤´ï¼Œه…¶ه‡؛هڈ£è¢«ن¸¥ه¯†çڑ„ه›½é™…وٹ€وœ¯ç®،هˆ¶هچڈè®®é™گهˆ¶ï¼Œه¯¹هچژه‡؛هڈ£و›´éœ€ç»ڈو¼«é•؟çڑ„ه±‚ه±‚ه®،و‰¹م€‚è؟™ه µو›¾ç»ڈهڑن¸چهڈ¯و‘§çڑ„“ه¢™â€ï¼Œه¦‚ن»ٹه·²è¢«38ه²پçڑ„“ه¼؛ه›½é’ه¹´ç§‘ه¦ه®¶â€وڈگهگچ者ه¾گه…ˆن¸œه¸¦éکںه‡؟ç©؟,èٹ±ن؛†ن¸¤ه¹´ه¤ڑçڑ„و—¶é—´م€‚

م€€م€€2025ه¹´â€œه¼؛ه›½é’ه¹´ç§‘ه¦ه®¶â€ه‘¨و–°é›¨و‰‹وŒپ“èژ«و¯”ن¹Œو–¯çژ¯â€ç؛ھه؟µه“پم€‚
م€€م€€â€œé،¶ه¤©ç«‹هœ°â€ 解ه†³é—®é¢ک
م€€م€€é‚£ن؛›â€œه¼؛ه›½é’ه¹´ç§‘ه¦ه®¶â€çڑ„ن¸“ن¸ڑ领هںںه’Œç§‘ç ”è·¯ه¾„هگ„ه¼‚,هچ´وœ‰ç€ç›¸ن¼¼çڑ„ç²¾ç¥ه؛•è‰²م€‚
م€€م€€â€œن¸€ن¸ھه¥½çڑ„ç§‘ç ”é،¹ç›®ï¼Œه؛”ه½“çœںو£è§£ه†³çژ°ه®ن¸–ç•Œçڑ„é—®é¢کم€‚â€ç½—ه‘¨هچ؟说,è؟‘ه¹´و¥ï¼Œه›½ه®¶ن¸€ç›´هœ¨وڈگه€،ç§‘ç ”è¦پ“é،¶ه¤©ç«‹هœ°â€ï¼Œن»–çڑ„çگ†è§£وک¯â€”—é،¶ه¤©ï¼Œوک¯وŒ‡ç§‘ه¦ه‰چو²؟çڑ„çھپç ´ن¸ژهˆ›و–°ï¼›ç«‹هœ°ï¼Œوک¯وŒ‡ç«‹è¶³ن؛؛类社ن¼ڑçڑ„ه®é™…需و±‚م€پ解ه†³ه®é™…é—®é¢کم€‚
م€€م€€هœ¨ç½—ه‘¨هچ؟看و¥ï¼Œهگˆوˆگç”ں物ه¦ن¸چن»…وک¯هں؛ç،€ç§‘ه¦çڑ„çھپç ´ï¼Œو›´ن¸؛هŒ»ه¦م€په†œن¸ڑم€پ能و؛گç‰é¢†هںںه¸¦و¥é©ه‘½و€§هڈ¯èƒ½م€‚“و¯”ه¦‚éپ—ن¼ ç—…و²»ç–—,ه¦‚وœوںگن¸ھهں؛ه› çھپهڈکه¯¼è‡´هٹں能ن¸§ه¤±ï¼Œوˆ‘ن»¬هڈ¯ن»¥é€ڑè؟‡هگˆوˆگوٹ€وœ¯â€کè،¥ه›â€™و£ه¸¸هں؛ه› ï¼›هœ¨è‚²ç§چن¸ٹ,وˆ‘ن»¬هڈ¯ن»¥وŒ‰éœ€è®¾è®،ن½œç‰©و€§çٹ¶ï¼Œه‘ٹهˆ«â€کé ه¤©هگƒé¥â€™م€‚â€
م€€م€€â€œه¦‚ن½•è§£ç”è؟™ن؛›ه®é™…çڑ„é—®é¢ک,وک¯éه¸¸é‡چè¦پçڑ„م€‚â€ç½—ه‘¨هچ؟و—¶ه¸¸ه’Œن»–çڑ„ه¦ç”ں谈,科ه¦é،»ç«‹è¶³ه½“ن¸‹ç¤¾ن¼ڑçڑ„ه®é™…需و±‚,وڈگه‡؛é—®é¢ک,ه¾ھه؛ڈو¸گè؟›هœ°è§£ه†³é—®é¢کم€‚“ن½ ه›´ç»•وœ‰ن»·ه€¼çڑ„ن؛‹ç‰©ï¼Œن»»ن½•ن¸€ç‚¹è؟›و¥ï¼Œéƒ½èƒ½ن½“çژ°ه‡؛éه¸¸ه¤§çڑ„ن»·ه€¼م€‚â€
م€€م€€é’ه¹´ç§‘ه¦ه®¶ه‘¨و–°é›¨هژںوœ¬ن»ژن؛‹ç¥ç»ڈç—…ه¦ç ”究,ن»–çڑ„ç§‘ç ”ن¹‹è·¯çڑ„转هڈک,ه§‹ن؛ژهœ¨é—¨è¯ٹè§پهˆ°çڑ„ن¸€ن¸ھ被وٹ‘éƒپç—‡وٹک磨çڑ„ه¥³ه©م€‚
م€€م€€é‚£ن¸ھه¥³ه©هڈھوœ‰هچپن¸‰ه››ه²پ,被父و¯چه¸¦و¥çœ‹ç—…,هچ´و€»ن½ژه¤´ن¸چè¯ï¼Œé»کé»کوµپو³ھم€‚ه‘¨و–°é›¨ن»ژه¥³ه©çˆ¶و¯چهڈ£ن¸ه¾—çں¥ï¼Œه¥¹ه·²ن¼‘ه¦ن¸€ه¹´م€‚父و¯چو’¸èµ·ه¥³ه©çڑ„袖هگو—¶ï¼Œه‘¨و–°é›¨çœ‹هˆ°ï¼Œه¥¹çڑ„و‰‹è‡‚ن¸ٹéپچه¸ƒن¼¤ç—•م€‚
م€€م€€هگژو¥ï¼Œه¥¹çڑ„父و¯چ递و¥ن¸€ه¼ ç؛¸و،,ن¸ٹé¢ه†™ç€ن¸€é¦–诗ï¼ڑ“ن½ وک¯هڈç§چهگ/ن¸چهڈ‘èٹ½/ن¸چé•؟ه¤§/ن¹ںن¸چ结وœ/ن½ 该被و‰“ç¢ژ/و¯èگژ/被烧焦ن¹ںو— ه¦¨/ه°±و°¸è؟œو´»هœ¨ه¤ç‹¬ن¸هگ§/ن½ ن¸چن¼ڑهڈکه¥½ï¼پâ€ç؛¸ن¸ٹ,è؟کç”»ç€ن¸چهڈ‘èٹ½çڑ„ç§چهگن¸ژو¯هڈ¶م€‚
م€€م€€é‚£é¦–诗ه¯¹ه‘¨و–°é›¨è§¦هٹ¨ه¾ˆه¤§ï¼Œâ€œه؟ƒçپµçڑ„وٹک磨و¯”è؛¯ن½“疼痛و›´éڑ¾هڈ—,ه› ن¸؛ه¤§ه®¶ن¸چçگ†è§£â€م€‚
م€€م€€ن»–至ن»ٹè®°ه¾—,ه½“è‡ھه·±وڈگه‡؛هژ»هŒ»é™¢ç²¾ç¥ç§‘ه·¥ن½œو—¶ï¼Œé™¢é•؟说“وˆ‘ه½“院é•؟ن¸€ن؛Œهچپه¹´ï¼Œن½ وک¯ç¬¬ن¸€ن¸ھن¸»هٹ¨و„؟و„ڈهژ»ç²¾ç¥ç§‘çڑ„â€م€‚ه®¶é‡Œن؛؛èµ·هˆن¹ںه¹¶ن¸چçگ†è§£ن»–çڑ„ه†³ه®ڑم€‚ه¯¹ن»–而言,è؟™ن¹ںوک¯ن¸€ن¸ھ相ه¯¹é™Œç”ںçڑ„领هںںم€‚
م€€م€€ه„؟ç«¥é’ه°‘ه¹´وٹ‘éƒپç—‡çڑ„è¯ٹç–—وک¯ن¸–ç•Œو€§éڑ¾é¢کم€‚ه‘¨و–°é›¨è،¨ç¤؛,ه„؟ç«¥وٹ‘éƒپç—‡çٹ¶ن¸چه…¸ه‹ï¼Œهڈ¯èƒ½è،¨çژ°ن¸؛ه¤´ç—›م€پ胃痛م€پوک“و€’,ç”ڑ至و”»ه‡»è،Œن¸؛م€‚و›´ن¸¥ه³»çڑ„وک¯ï¼Œèچ¯ç‰©و²»ç–—ه¯¹ه„؟ç«¥و•ˆوœوœ‰é™گ,ن¸”هڈ¯èƒ½ه¢هٹ è‡ھو€é£ژ险م€‚2016ه¹´ï¼Œن»–çڑ„ه›¢éکںé€ڑè؟‡ç ”究هڈ‘çژ°ï¼Œهœ¨12ç§چوٹ—وٹ‘éƒپèچ¯ن¸ن»…وœ‰1ç§چه¯¹é’ه°‘ه¹´هڈ¯èƒ½وœ‰و•ˆم€‚
م€€م€€ه‘¨و–°é›¨ن¸€ç›´هœ¨çگ¢ç£¨ï¼Œه„؟ç«¥é’ه°‘ه¹´وٹ‘éƒپç—‡çڑ„è¯ٹو–وœ‰و²،وœ‰ه®¢è§‚وŒ‡و ‡ï¼Œو²»ç–—وک¯هگ¦وœ‰و–°و–¹و،ˆم€‚
م€€م€€â€œçژ°هœ¨çڑ„é—®é¢کوک¯ï¼Œه„؟ç«¥é’ه°‘ه¹´وٹ‘éƒپ症,ن¸»è¦پوک¯é€ڑè؟‡é‡ڈè،¨و¥è؟›è،Œç›وں¥ï¼Œن½†ه®ƒçڑ„ه‡†ç،®و€§ن¸چوک¯ه¾ˆه¥½م€‚â€ه‘¨و–°é›¨ه‘ٹ诉记者,ن¼´éڑڈç€وٹ‘éƒپç—‡هœ¨é’ه°‘ه¹´ç¾¤ن½“ن¸هڈ‘ç—…çژ‡وڈگé«ک,ه¦‚ن½•وٹٹوœ‰وƒ…ç»ھé—®é¢کçڑ„ه©هگهڈٹو—¶è¯†هˆ«ه‡؛و¥ï¼Œوˆگن¸؛è؟«هˆ‡è¦پ解ه†³çڑ„社ن¼ڑé—®é¢کم€‚
م€€م€€â€œوˆ‘ن»¬ه؟…é،»و‰¾هˆ°و›´ه®¢è§‚م€پو›´ç²¾ه‡†çڑ„è¯ٹو–و–¹ه¼ڈم€‚â€ه‘¨و–°é›¨ه›¢éکںèپ”هگˆن¸ه›½ç§‘ه¦é™¢م€پهŒ—ن؛¬هچڈه’ŒهŒ»é™¢ç‰وœ؛و„,ن»ژè،€وµ†ن¸ç›é€‰ه‡؛3ç§چç”ں物و ‡ه؟—物,ه¹¶هں؛ن؛ژ该وˆگوœه¼€هڈ‘ن؛†ç‰¹ه¼‚è¯ٹو–试ه‰‚盒,ن¸؛ه„؟ç«¥é’ه°‘ه¹´وٹ‘éƒپ症精ه‡†è¯ٹو–وڈگن¾›ن؛†و–°و€è·¯م€‚
م€€م€€â€œوˆ‘ن»¬ن»ژ4000ه¤ڑç§چ物质ن¸ه±‚ه±‚ç›é€‰ï¼Œوœ€ç»ˆé”په®ڑ3ç§چم€‚è؟™ن¸ھè؟‡ç¨‹ï¼Œèٹ±ن؛†و•´و•´6ه¹´م€‚â€ه‘¨و–°é›¨ه‘ٹ诉记者م€‚
م€€م€€â€œè¦پوٹٹè‡ھه·±çڑ„科ه¦ç ”究ن¸ژن¸´ه؛ٹه®è·µç»“هگˆèµ·و¥ï¼Œè؟™و ·و‰چ能ه¤ںوœچهٹ،و‚£è€…,وœچهٹ،ه¤§ن¼—م€‚â€ه‘¨و–°é›¨è¯´ï¼Œن¸€ن¸ھه†œو°‘هپڑه¾—ه†چه¥½ï¼Œهڈھ能ç§چن¸€ن؛©ن¸‰هˆ†هœ°ï¼Œه¦‚وœوˆگن¸؛هƒڈè¢پéڑ†ه¹³ن¸€و ·çڑ„科ه¦ه®¶ï¼Œه°±èƒ½و”¹è‰¯ç§چهگï¼Œé€ ç¦ڈهچƒهچƒن¸‡ن¸‡è€پ百ه§“م€‚
م€€م€€ه¦‚ن»ٹ,ن»–牵ه¤´هœ¨é‡چه؛†هگ„هŒ؛هژ؟82و‰€ه¦و ،ه»؛ç«‹ç›وں¥ç½‘络,وژ¨هٹ¨وٹ‘éƒپç—‡و—©وœں识هˆ«è؟›ه…¥و ،ه›ن½“و£€م€‚ه‘¨و–°é›¨è¯´ï¼ڑ“وˆ‘ن¸€è¾ˆهگوœ€ه¤ڑ看10ن¸‡ن¸ھç—…ن؛؛,ن½†ن¸€é،¹و–°وٹ€وœ¯èƒ½وƒ هڈٹ百ن¸‡هچƒن¸‡ï¼Œç”ڑ至و›´ه¤ڑن؛؛م€‚â€
م€€م€€èژ·ه¾—“ه¼؛ه›½é’ه¹´ç§‘ه¦ه®¶â€وڈگهگچçڑ„ن؛‘هچ—ه¤§ه¦و•™وژˆéں©é¹ڈن¹ںوœ‰ç±»ن¼¼çڑ„وƒ³و³•م€‚
م€€م€€ن»–وک¯ه†œو°‘çڑ„ه©هگ,وک¯è؟™ç¾¤é’ه¹´ç§‘ه¦ه®¶ن¸ه°‘وœ‰çڑ„ن»ژن؛‹ه†œن¸ڑç§‘ç ”çڑ„ن؛؛م€‚用ن»–è‡ھه·±çڑ„è¯è¯´ï¼Œن»–وک¯çœںو£وٹٹç§‘ç ”و–‡ç« ه†™هœ¨ن؛†ه¤§هœ°ن¸ٹم€‚و¯ڈه¹´ï¼Œن»–都ن¼ڑèٹ±ه¤§é‡ڈو—¶é—´ن¸‹ن¹،è°ƒç ”ï¼Œو·±ه…¥ç”°é—´هœ°ه¤´ï¼Œé€ڑè؟‡ه¼€ه±•ç”°é—´è¯•éھŒوژ¨هٹ¨ه†œن¸ڑه…¥ن¾µه®³è™«çڑ„ç»؟色éک²وژ§م€‚
م€€م€€وœ‰و—¶ï¼Œن»–هژ»ه†œو‘è°ƒç ”ï¼Œو€»وœ‰ه†œوˆ·é—®ن»–ه†œç”°é‡Œو€¥éœ€è§£ه†³çڑ„ن؛‹م€‚ن»–و—¶ه¸¸è¢«ه†œوˆ·é—®è’™ï¼Œن¸چçں¥ه¦‚ن½•ه›ç”,و€»è§‰ه°´ه°¬م€‚éں©é¹ڈن¸چه¸Œوœ›è‡ھه·±وˆگن¸؛â€œç –ه®¶â€ï¼Œè€Œوک¯è¦پهپڑن¸€ن؛›و›´ه®é™…çڑ„ç§‘ç ”م€پ能èگ½هœ°çڑ„ه؛”用,让è€پ百ه§“هڈ—ç›ٹم€‚
م€€م€€2017ه¹´ï¼Œن»–هœ¨ن¸ه›½ç§‘ه¦é™¢و–°ç–†ç”ںو€پن¸ژهœ°çگ†ç ”究و‰€ه·¥ن½œو—¶ï¼Œو£وک¯ç•ھ茄و½œهڈ¶è›¾ن»ژوˆ‘ه›½è¥؟هŒ—ه…¥ن¾µو‰©و•£çڑ„و—¶وœں,ه¯¹وˆ‘ه›½çڑ„ç•ھ茄ن؛§ن¸ڑé€ وˆگه·¨ه¤§ه¨پèƒپم€‚هœ¨éƒ¨هˆ†هœ°هŒ؛,ç•ھ茄و½œهڈ¶è›¾çڑ„هچ±ه®³çژ‡ن¸€ه؛¦é«کè¾¾60%,ن¼ڑé€ وˆگ80%çڑ„ه‡ڈن؛§ï¼Œè®¸ه¤ڑه†œوˆ·ه¾ˆو— ه¥ˆï¼Œن¼ ç»ںهŒ–ه¦èچ¯ه‰‚ه·²ه¾ˆéڑ¾وٹ‘هˆ¶è؟™ç§چ虫هگم€‚
م€€م€€â€œè™«هگهœ¨è؟›هŒ–,ه®ƒن؛§ç”ںن؛†è€گèچ¯و€§م€‚â€éں©é¹ڈ说,هڈھه¥½ه°è¯•ç”ں物éک²و²»ï¼Œن»¥è™«و²»è™«م€‚ن»–ن»¬هڈ‘çژ°ç•ھ茄ن½œç‰©ن¸ٹهژںوœ¬هکهœ¨ن¸€ç§چهڈ«â€œçƒں盲è½â€çڑ„و‚é£ںو€§ه¤©و•Œï¼Œه®ƒو—¢èƒ½é«کو•ˆوچ•é£ںç•ھ茄و½œهڈ¶è›¾çڑ„虫هچµه’Œه¹¼è™«ï¼Œè؟ک能ن¾é هڈ–é£ںç•ھ茄و¤چو ھ而هکو´»م€‚
م€€م€€è€Œهگژ,ه›¢éکںé€ڑè؟‡è°ƒوژ§ç•ھ茄و–½è‚¥وٹ€وœ¯و–¹و،ˆï¼Œè®©â€œçƒں盲è½â€هœ¨ن¸چهچ±ه®³ç•ھ茄و¤چو ھçڑ„ه‰چوڈگن¸‹ï¼Œوœ‰و•ˆوژ§هˆ¶ن½ڈç•ھ茄و½œهڈ¶è›¾çڑ„ç§چ群وڑ´هڈ‘م€‚ç»ڈè؟‡ن¸‰ه››ه¹´çڑ„هٹھهٹ›ï¼Œن»–ن»¬ه°†ç•ھ茄و½œهڈ¶è›¾çڑ„هچ±ه®³çژ‡é™چن½ژ至20%ه·¦هڈ³م€‚
م€€م€€2024ه¹´ï¼Œن»–çڑ„ه›¢éکںèپ”هگˆو³•ه›½م€پç¾ژه›½م€پو¾³ه¤§هˆ©ن؛ڑه’Œه›½ه†…çڑ„ن¸“ه®¶é¦–و¬،وڈگه‡؛“3MPوٹ€وœ¯و¨،ه¼ڈâ€â€”—“ه¤ڑه®³è™«ه¤ڑç»´و²»çگ†â€وٹ€وœ¯و¨،ه¼ڈ,و ¸ه؟ƒوک¯é›†وˆگ“هœںه£¤è°ƒوژ§+ن¼´ن¾£و¤چ物+ن»¥è™«و²»è™«â€çڑ„وٹ€وœ¯و¨،ه¼ڈم€‚ه¦‚ن»ٹ,ن»–ه’Œه›¢éکںه·²هœ¨وˆ‘ه›½ن؛‘هچ—م€په±±ن¸œç‰هœ°هŒ؛,ن»¥هڈٹو³°ه›½م€پè¶ٹهچ—م€پè¥؟çڈ牙ç‰ه›½ه»؛ç«‹ن؛†è¯•éھŒç‚¹ï¼Œوژ¨هٹ¨وٹ€وœ¯èگ½هœ°م€‚
م€€م€€â€œهœ¨ن؛‘هچ—ه³¨ه±±ï¼Œوˆ‘ن»¬ه¸®هٹ©ه†œوˆ·ه°†هŒ–ه¦ه†œèچ¯ه‡ڈé‡ڈ40%,ن¹ںن؟è¯پن؛†ç•ھ茄ن؛§é‡ڈم€‚â€éں©é¹ڈه‘ٹ诉记者م€‚ن¸‹ن¸€و¥ï¼Œن»–è®،هˆ’وژ¨هٹ¨هں؛ن؛ژ3MPوٹ€وœ¯و¨،ه¼ڈçڑ„ç»؟色ه†œن؛§ه“پ认è¯پ,让é€ڑè؟‡è¯¥و¨،ه¼ڈç”ںن؛§çڑ„ç•ھ茄ه®çژ°و؛¢ن»·é”€ه”®ï¼Œن»ژه¸¸è§„ه†œن؛§ه“پèµ°هگ‘ç»؟色ه†œن؛§ه“پم€‚
م€€م€€â€œوˆ‘ن»¬çڑ„ç›®و ‡ن¸چوک¯ه®Œه…¨و¶ˆçپه®³è™«ï¼Œè€Œوک¯é€ڑè؟‡ç”ںو€پè°ƒوژ§و‰‹و®µï¼Œه°†ه…¶وژ§هˆ¶هœ¨ç»ڈوµژéکˆه€¼ه†…م€‚â€éں©é¹ڈ说,“ه†œن¸ڑوٹ€وœ¯ه؟…é،»è½»ç®€هŒ–م€پهڈ¯وژ¨ه¹؟,è€پ百ه§“用ه¾—èµ·م€پو„؟و„ڈ用م€‚â€
م€€م€€هœ¨éں©é¹ڈçڑ„ç§‘ç ”ن¸–界里,هˆ›و–°ن¸ژèگ½هœ°ه¹¶é‡چم€‚وœھو¥ï¼Œن»–ه¸Œوœ›è؟™ه¥—ç”ںن؛§وٹ€وœ¯و¨،ه¼ڈه…ˆè®©ç§چç•ھ茄çڑ„ه†œو°‘هڈ—ç›ٹ,而هگژé€گو¥ه®Œه–„çگ†è®؛و–¹و³•ï¼Œوœ€ç»ˆè®©ه›½ه†…ه¤–çڑ„ه…¶ن»–ه†œن½œç‰©هœ¨è™«ه®³éک²وژ§ن¸éƒ½ç”¨ه¾—ن¸ٹم€‚
م€€م€€و•¢ن؛ژه¤±è´¥ ن؟وŒپه¥½ه¥‡
م€€م€€è؟™ن؛›ه¹´è½»ç§‘ه¦ه®¶çڑ„ç§‘ç ”ن¹‹è·¯ï¼Œه¹¶é轻而وک“ن¸¾ه°±èژ·ه¾—وˆگهٹں,许ه¤ڑن؛؛都هژ†ç»ڈو— و•°و¬،ه¤±è´¥م€‚
م€€م€€ç„¶è€Œï¼Œç½—ه‘¨هچ؟هڈ‘çژ°ï¼Œو— è®؛وک¯ç§‘ه¦ن¼ و’,è؟کوک¯ه¦وœ¯هˆ†ن؛«م€په¤§ه¦و•™è‚²ï¼Œن؛؛ن»¬و€»çƒè،·ن؛ژè°ˆè®؛وˆگهٹں,هچ´ن¸چو€ژن¹ˆوڈگهڈٹه¤±è´¥م€‚
م€€م€€â€œن¸چè¦په®³و€•ه¤±è´¥م€‚â€ç½—ه‘¨هچ؟说,هپڑç§‘ç ”è¦پوœ‰وپه¼؛çڑ„è€گه؟ƒï¼Œه¾ˆهڈ¯èƒ½ن¸€ن¸ھé،¹ç›®èٹ±è´¹ن؛†5ه¹´ï¼Œه‰چوœں99%çڑ„هپڑو³•éƒ½وک¯هœ¨è¯•é”™ï¼Œâ€œهڈھè¦پ积累هˆ°ن¸€ه®ڑو•°é‡ڈçڑ„错误,那ن¹ˆوˆ‘ن»¬هœ¨ç¬¬ه››ه¹´ه¹´ه؛•ه°±وœ‰هڈ¯èƒ½é،؟و‚ںâ€م€‚
م€€م€€ن»–è®°ه¾—,ه½“هˆهڈ‚ن¸ژçœںو ¸ç”ں物هں؛ه› 组هگˆوˆگè®،هˆ’çڑ„é،¹ç›®ï¼Œه®éھŒه‰چهگژهپڑن؛†3و¬،,ه‰چن¸¤و¬،都ه¤±è´¥ن؛†ï¼Œو¯ڈهپڑن¸€و¬،è¦پ耗费ن¸€ه¹´è‡³ه‡ ه¹´çڑ„و—¶é—´ï¼Œوœ€هگژن¸€و¬،و‰چوˆگهٹںم€‚ن½†ن»–هڈ‘çژ°ï¼Œه¦‚ن»ٹçڑ„و•™è‚²è®©ه¦ç”ںن¹ںهڈھè®°ه¾—وˆگهٹںçڑ„ن¸œè¥؟,ه¾ˆه°‘هژ»ه…³و³¨ه¤±è´¥م€‚
م€€م€€â€œه¤±è´¥çڑ„ç»ڈéھŒï¼Œو²،وœ‰ه¾ˆه¥½هœ°ن¼ و‰؟م€‚â€ç½—ه‘¨هچ؟ه‘ٹ诉记者,ه…¶ه®è®¸ه¤ڑ科ه¦ه®¶ç»ڈهژ†è؟‡ه¤§é‡ڈçڑ„试错م€په¤±è´¥ï¼Œè؟™ن؛›è؟‡ç¨‹هگŒو ·ه¾ˆوœ‰و„ڈن¹‰ï¼Œè؟™هڈ¯ن»¥éپ؟ه…چو›´ه¤ڑن؛؛èµ°ه¼¯è·¯ï¼Œâ€œهچ³ن½؟وک¯éک´و€§ï¼ˆه®éھŒï¼‰ç»“وœï¼Œن¹ںه…·وœ‰ه·¨ه¤§çڑ„ن»·ه€¼â€م€‚
م€€م€€â€œç§‘ç ”ه·¥ن½œï¼Œç»ه¤§ه¤ڑو•°و—¶é—´وک¯هœ¨é¢ه¯¹ه¤±è´¥ه’Œوœھçں¥م€‚â€وژé›ھو¢…觉ه¾—,و²،وœ‰ن¸€ن»½ه†…هœ¨çڑ„驱هٹ¨هٹ›ه’Œه¯¹çœںçگ†çڑ„ç؛¯ç²¹è؟½و±‚,وک¯ه¾ˆéڑ¾هڑوŒپن¸‹هژ»çڑ„م€‚هœ¨è؟›è،Œâ€œو°´ن¼ڈو•ˆه؛”â€ç ”究çڑ„و—©وœں,ن»–ن»¬ه›¢éکں设è®،çڑ„ه™¨ن»¶è¾“ه‡؛电هژ‹éه¸¸ن½ژ,ن¸€ç›´ه¾که¾ٹهœ¨و¯«ن¼ڈé‡ڈç؛§ï¼Œن¸€ه؛¦éه¸¸ç„¦è™‘,ن»؟ن½›èµ°ه…¥ن؛†ن¸€و،و»èƒ،هگŒم€‚
م€€م€€é‚£و®µو—¶é—´ï¼Œوژé›ھو¢…ه’Œه›¢éکںè؟›è،Œن؛†و— و•°و¬،çڑ„ه°è¯•ï¼Œç»“وœو€»وک¯ن¸چçگ†وƒ³م€‚هگژو¥ï¼Œن»–ن»¬ه†³ه®ڑوڑ‚و—¶و”¾ن¸‹ه¯¹و€§èƒ½çڑ„盲目è؟½و±‚,é‡چو–°و·±ه…¥وژ¢ç©¶ه…¶èƒŒهگژçڑ„物çگ†وœ؛هˆ¶ï¼Œن»ژه¤´و„ه»؛çگ†è®؛و¨،ه‹م€‚
م€€م€€â€œو£وک¯é‚£و¬،看ن¼¼â€که€’退’çڑ„ه½’零و€è€ƒï¼Œè®©وˆ‘ن»¬و‰¾هˆ°ن؛†و£ç،®çڑ„و–¹هگ‘,ه®çژ°ن؛†ن¹‹هگژçڑ„و€§èƒ½é£è·ƒم€‚â€وژé›ھو¢…说,“و‰€ن»¥ï¼Œç§‘ç ”ن¸çڑ„ه¤±è´¥ه¾€ه¾€وک¯é€¼وˆ‘ن»¬ه›ه½’وœ¬è´¨م€په¯»و‰¾çœںçگ†çڑ„ه¥‘وœ؛م€‚â€
م€€م€€è®¸ه¤ڑé’ه¹´ç§‘ه¦ه®¶هڈ—è®؟و—¶ï¼Œè؟که¸¸وڈگهڈٹ“ه¥½ه¥‡â€â€œه…´è¶£â€ن¸¤ن¸ھè¯چم€‚
م€€م€€وژé›ھو¢…说,ه¥¹ن»ژه°ڈه¯¹â€œن¸؛ن»€ن¹ˆن¸چهگŒوگو–™وœ‰ن¸چهگŒçڑ„و€§èƒ½â€ه……و»،ه¥½ه¥‡ï¼Œو±‚ه¦وœں间,وژ¥è§¦هˆ°هٹ›ه¦ن¸ژوگو–™çڑ„ن؛¤هڈ‰ç ”究,هڈ‘çژ°é€ڑè؟‡è®¾è®،وگو–™è،¨é¢ï¼Œهڈ¯ن»¥è§£ه†³èˆھç©؛èˆھه¤©ن¸çڑ„ه…³é”®é—®é¢ک,“è؟™ç§چن»ژه¾®è§‚هˆ°ه®ڈ观çڑ„è·¨è¶ٹ让وˆ‘و·±و·±ç€è؟·â€م€‚
م€€م€€èژ·ه¾—2025ه¹´â€œه¼؛ه›½é’ه¹´ç§‘ه¦ه®¶â€وڈگهگچçڑ„ه¾گه…ˆن¸œï¼Œه°†è‡ھه·±ç§‘ç ”çڑ„ه؟«é€ںçھپç ´ï¼Œé¦–ه…ˆه½’هٹںن؛ژè‡ھه·±ه¯¹ç§‘ç ”و–¹هگ‘çڑ„ç؛¯ç²¹ه…´è¶£ï¼Œن»¥è‡³ن؛ژن»–هœ¨هژںهگن¸–界里è¶ٹé’»è¶ٹو·±م€‚ه¤ڑه¹´و¥ï¼Œن»–ه¯¹وگو–™ن¸–ç•Œو€»و€€وœ‰ن¸€ç§چ“هˆ¨و ¹é—®ه؛•â€çڑ„و¸´وœ›ï¼Œè؟™ن¹ںوˆگن¸؛ن»–ç§‘ç ”ن¹‹è·¯ن¸ٹç»ڈن¹…ن¸چوپ¯çڑ„燃و–™م€‚
م€€م€€ç½—ه‘¨هچ؟çڑ„ç§‘ç ”ن¹‹è·¯ï¼Œن¹ںه±ن؛ژه…´è¶£ه¯¼هگ‘ه‹م€‚ن»–ن»ژé«کن¸ه¼€ه§‹ï¼Œه°±ه–œو¬¢ç”ں物,ه–œو¬¢وژ¢ç´¢وœھçں¥é¢†هںں,هچ³ن¾؟هœ¨ه¤–ن؛؛看و¥و¯ç‡¥و— ه‘³م€‚ن»–هڈ‘çژ°ï¼Œه½“è‡ھه·±ه¯¹وںگن¸€é¢†هںںو„ںه…´è¶£و—¶ï¼Œه¦èµ·و¥ه¾ˆè½»و¾م€‚
م€€م€€ن»–ه¸¸ه’Œه¦ç”ںن»¬è°ˆï¼Œه¹¶éهڈھوœ‰ن»ژن؛‹ç§‘ç ”م€پوˆگن¸؛科ه¦ه®¶و‰چوœ‰ن»·ه€¼ï¼Œè¦پو‰¾هˆ°è‡ھه·±çœںو£و„ںه…´è¶£ن¸”وœ‰و„ڈن¹‰çڑ„ن؛‹ن¸ڑم€‚ه¾ˆه¤ڑو—¶ه€™ï¼Œن»–选و‹©ه¦ç”ںçڑ„و ‡ه‡†ن¹ںهŒ…و‹¬ï¼Œه¯¹و‰€هœ¨é¢†هںںçœںو£و„ںه…´è¶£ï¼Œè؟™و ·و‰چن¼ڑه°†ه…´è¶£è½¬هŒ–ن¸؛ن¸چو–وژ¢ç´¢çڑ„هٹ¨هٹ›ï¼Œو‰چن¼ڑوœ‰ن¸»هٹ¨و€§م€‚
م€€م€€â€œن¸چè¦پن»…ه› ن¸؛وںگن¸ھو–¹هگ‘çƒé—¨وˆ–ه‰چو²؟,ه°±ç›²ç›®è·ںéڑڈهˆ«ن؛؛,è؟™ç§چè،Œن¸؛é€ڑه¸¸ن¼ڑه¯¼è‡´è‡ھه·±éه¸¸ç—›è‹¦م€‚â€ç½—ه‘¨هچ؟说م€‚
م€€م€€هœ¨وژé›ھو¢…看و¥ï¼Œç§‘ç ”وک¯ن¸€هœ؛وŒپن¹…وˆک,ه¥¹وœ€çœ‹é‡چه¦ç”ںçڑ„ه¥½ه¥‡ه؟ƒن¸ژéں§و€§م€‚“وœ‰ه¥½ه¥‡ه؟ƒï¼Œو‰چن¼ڑن¸»هٹ¨هژ»è؟½é—®ن¸؛ن»€ن¹ˆï¼Œè؟™وک¯هˆ›و–°çڑ„و؛گه¤´ï¼›وœ‰éں§و€§ï¼Œو‰چ能هœ¨ن¸€و¬،و¬،ه®éھŒه¤±è´¥هگژ,ن¾ç„¶وœ‰ه‹‡و°”站起و¥é‡چو–°ه¼€ه§‹م€‚â€
م€€م€€ن¸é’وٹ¥آ·ن¸é’网记者 وژه¼؛ 陈و™“و¥و؛گï¼ڑن¸ه›½é’ه¹´وٹ¥
م€€م€€2025ه¹´10وœˆ31و—¥ 06版





 ن؛¬ه…¬ç½‘ه®‰ه¤‡ 11010102004843هڈ·
ن؛¬ه…¬ç½‘ه®‰ه¤‡ 11010102004843ه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