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科学活力的源泉,预判科学发展的走向
发稿时间:2022-06-24 11:01:00 作者:李文靖 来源: 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学界新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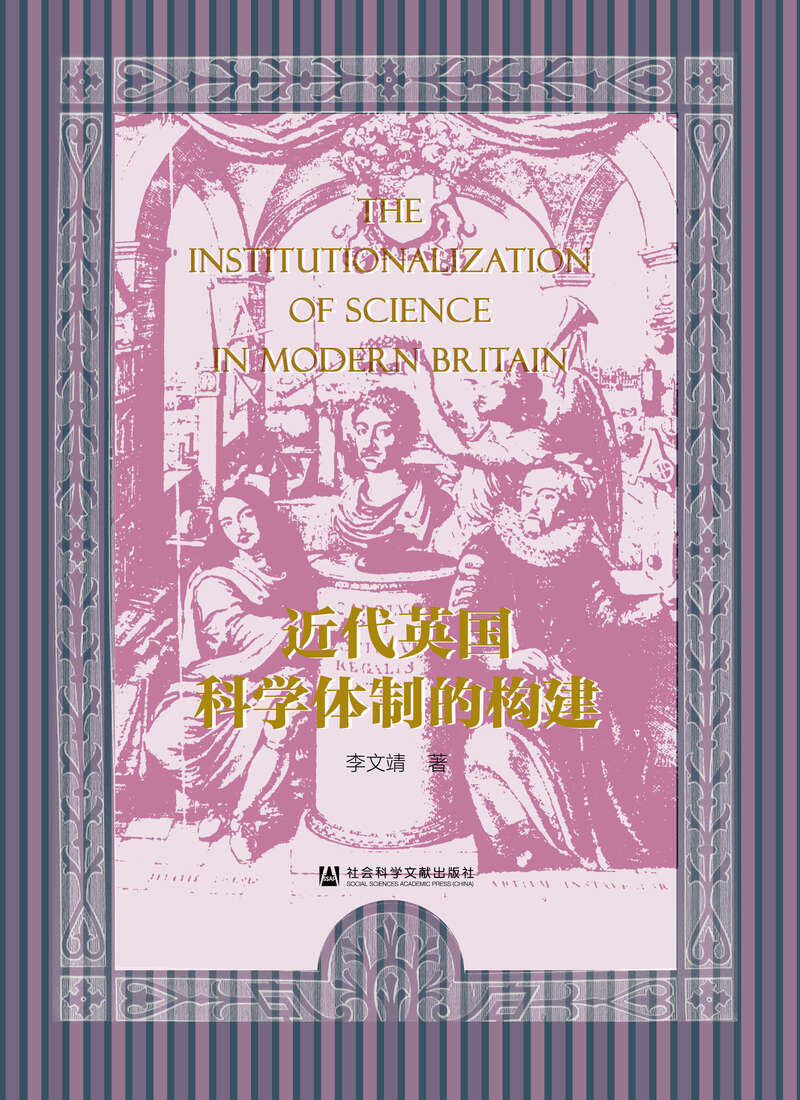
《近代英国科学体制的构建》书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供图
从16世纪下半叶英国知识阶层接纳和推崇实验科学方法论,到19世纪中叶英国政府作为公众的代理人聘用科学家和为科学活动出资,英国完成了科学建制化的早期阶段,初步形成了今天意义上的公共科学体制。这段历史可以看作科学在英国社会和文化条件下展开和实现其内在本质的过程。科学建制化的共性和个性都可以从这段历史中一窥究竟。
科学建制化的共性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实验科学方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得到社会承认。经验事实成为真理标准有着历史必然性,如宗教改革的影响,但是不具备认识论上的必然性,后一点从经验论和唯理论的长期争论中便可以看出。
第二,实验科学这种特殊的认知方法本身决定了它的公共属性。实验借助工具和仪器对经验事实进行预定和操控,本质上是将个别经验转化为集体经验的过程。而个别经验的来源、工具仪器的制造与改进以及集体经验的传播和强化等,无不需要外在社会文化资源与物质资料的输入。这也解释了科学为什么是一种代价高昂、极具消耗性的实践活动。
第三,科学的公共性可以大致分为内部公共性和外部公共性。内部公共性涉及科学共同体的形成、科学评价机制、科学组织结构等。外部公共性包含科学资助体系下科学家的政治参与、科学的技术化和社会化、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等。如果对科学建制化下一个定义,它应该是科学这样一种特殊的认知方法通过组织化、政治化、社会化、技术化和职业化的途径,逐步展开和实现其公共性的过程。
第四,科学在理论、实验操作和体制三个层面的历史发展相互交织、相互匹配、不可分割。例如,科学组织模式能够影响科学理论产出,专职科学家更有可能取得数学和理论物理学的突破,而业余科学家往往首选自然志。例如,科学家用新科学仪器得到新的科学发现,而科学家能否得到新科学仪器又取决于科学资助制度形式。再如,科学知识的分野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科学组织的分化。
第五,科学家这一社会精英角色的出现,是历史上科学人的自我定位与外在的社会期望不断博弈、最终达成一致的结果。自然研究者不再是古代讲经传道的学人、智者和哲学家,也不再是近代早期乐于动手做实验和野外探险考察的航海者、绘图员、化学家、医生、商人、官员,而是休厄尔造出的新英文词“scientists”特指的对象。科学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看似是一个去中心的过程,即科学从近代早期少数人的智力游戏、怡情享受、交际话题,变成了令许多现代社会成员忙忙碌碌的庞然大物,实际上是知识权威为庞大的科学家群体所共同享有,只不过科学共同体内部又采取技术化的分工形式,才显得今天个体科学家的地位不及历史上的精英科学家。
第六,经验事实、科学人和科学体制构成了推动科学史的正题、反题与合题。科学人对经验事实做出回应,这个经验事实不单纯是自然,也不单纯是通过工具仪器观察到的现象,还包括时代大潮带来的文化呼声与社会需求。这一回应的结果是一定的科学体制形成的,特定的科学体制又规定了新的经验事实。矛盾运动,周而复始,推动历史。唯一不变的是人们做出回应的主动性,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先贤所说的推动他者却不为他者所动的“火”。
英国科学发展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培根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实验科学方法。皇家学会的成立让科学知识的生产、累积和传播变得有组织性。知识权威与国王和政府的政治权力不断互动,这种互动在英国内战、王朝复辟、殖民扩张和北美独立战争背景下表现明显。工业革命时期的生产发展和社会转型创造出对于科学的巨大需求。最后,一类接受科学分科教育和专业水平遴选的科学家出现了。他们被要求服务于公众,并接受公众的资助。
第二,如果将科学建制化的几种要素在各国之间进行比较,则可以粗略看出历史上英国科学体制的特点。英国和法国的科学组织化同时发生,但是路径不同。皇家学会实行松散的会员制,沿袭文艺复兴晚期以来的私人资助制度和业余研究传统,研究课题宽泛,在庞大的科学共同体内发起同行评议,首创权之争较多;巴黎科学院由政府拨款和管理,组织严整,课题集中,理论范式之争较多。法国模式接近于今天的科研院所,也更符合培根对所罗门宫的设想;英国模式却有其自洽的逻辑,政府无为、学人自助的方式在历史上被认为有利于保护科学机构的独立性和科学研究的创造性。至于哪一种组织模式可以带来更高的科学产出,要视具体的学科特点和发展阶段而言。19世纪,英国尽管在理论力学和数学方面不及法国,却在自然志方面保持领先地位。
第三,英国科学的政治化反映为科学家个人积极参与政治事务:维护王权、协助政府、推动改革和扩大殖民地等。这种积极性与历史上科学人物强调的自助和自主似乎是矛盾的,或许可以解释为尚未获得明确社会角色的科学人争取外界认可的一种努力。法国科学家的政治参与同样是主动而活跃的,拉普拉斯、夏普塔尔在法国政界的影响不亚于班克斯在英国的影响。不过,法国科学家群体、科学机构与政治的联系似乎更为紧密,如法国大革命对巴黎科学院、拿破仑战争对巴黎理工学校和巴黎高师的影响。
第四,英国科学的社会化程度超过了同一时期的法国,这是它率先启动工业革命和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结果。应该看到,“英国科学衰落论”也是科学社会化推进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近代英国的政治改革、思想转变和社会转型一样,英国科学的建制发展也显示出一种新旧调和、缓慢推进的趋势。科学体系中的私人、业余者、个体、贵族等要素始终存在,但是科学职业和公共科学制度又要破茧而出,两者之间的矛盾在19世纪上半叶国际竞争和国内政治改革的背景下进一步激化了,遂表现为皇家学会成立之初的信条受到质疑,唱衰之声不绝于耳。
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科学突飞猛进,私人和业余传统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20世纪的大科学模式更是对科学投入和科学组织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但是,进入21世纪,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发展让科学体制的灵活性和多样性重新引发人们的注意。过细、过窄的分科和专业化在应对不断“熵增”的经济活动与社会实践时也显示出乏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以史为鉴,既不需要过于强调要在业余科学传统自身框架内对其进行考察,也不强求一定要从历史上找出一些要素或者规律,补贴给现下的科学文化和科技政策。或许我们应该借用“筏喻”,先跳出原来过度简化的科学观,真正把握科学的流变、复杂、社会化本质,再基于本国具体实践,寻求科学活力的源泉,预判科学发展的走向。(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9-2011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科学史系客座研究员,2017-2018年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史系访问学者;本文经授权摘编自《近代英国科学体制的构建》一书结语,现标题系编者所加)
-
【海运仓暗房】第十七期:老照片里的中青报印刷厂
1953年,报社决定自建印刷厂,先是买下前门外琉璃厂一家私人开设的铸字厂,铸出了铅字,立起...
2022-06-24 12:32:00 -
7月1日起 上海将调整部分民生保障待遇标准
记者今天从上海人社局了解到,从7月1日起,上海将调整失业保险金和工伤保险待遇标准。自2022...
2022-06-24 12:29:00 -
西安一幼儿园百余名儿童感染沙门氏菌 园方被立案调查
近日,陕西西安一幼儿园百余名儿童出现身体不适症状,6月23日,莲湖区疾控中心表示,初步判定...
2022-06-24 11:54:00 -
河北三河一商户发生液化石油气瓶爆燃事故 10人受伤
据“网信三河”微信公众号消息,6月24日9时18分,河北省三河市福成尚街时代广场一商户发生液...
2022-06-24 11:54:00 -
吉林省将打造现代新型汽车和零部件万亿级大产业
日前,中共吉林省委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吉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省委十二届一次全会相关情...
2022-06-24 11:24:00 -
云南推进溯源治理 减少和预防寄递违禁品犯罪案件
2021年1月至2022年5月,云南检察机关共受理提请批准逮捕毒品犯罪案件4286件5488人,审查批准...
2022-06-24 10:58:00 -
2019年至2022年3月,检察机关起诉涉新型毒品犯罪16万多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厅厅长元明24日介绍,2019年至2022年3月,全国检察机关起诉涉新型毒品...
2022-06-24 10:54:00 -
乌克兰终于拿到入欧“号码牌”,但挑战才刚刚开始
当地时间6月23日,乌克兰终于拿到加入欧盟的排队“号码牌”,正式成为欧盟候选国。乌克兰总统...
2022-06-24 10:48:00 -
海报|乡村振兴 托起百姓安居乐业新生活
青翠的茶园,在山峦间铺展。不远处的学校,传来琅琅读书声。白墙黛瓦的搬迁移民小区里,老人...
2022-06-24 10:42:00 -
河北三河:燕郊一商业街商铺发生爆炸
6月24日上午,河北三河燕郊一商业街商铺发生爆炸,现场有市民受伤。据了解,事发地为当地福成...
2022-06-24 10:26:00 -
青平: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近日,习近平同志《论党的青年工作》出版发行,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文...
2022-06-24 10:12:00 -
青平:以“大国‘粮’策”托起百姓“稳稳的饭碗”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2022-06-24 10:03:00 -
青平:坚持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
6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
2022-06-24 10:03:00 -
青平:筑牢美好生活的安全基石
安全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
2022-06-24 10:03:00 -
FIFA:卡塔尔世界杯各队参赛大名单扩充至最多26人
国际足联24日官方宣布,在今年卡塔尔世界杯当中,各队参赛大名单由以往的23人扩大到最多26人...
2022-06-24 09:33:00 -
今年华南“龙舟水”为何那么强?专家解读原因
每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为华南前汛期的降水集中期,因为降雨期正好在端午节前后,又称为“龙舟...
2022-06-24 09:25:00 -
国家卫健委:昨日新增本土“18+26”例
6月23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7例。
2022-06-24 09:09:00 -
普京签令后,俄用卢布还债 警告西方再“闹”或断交!
日前,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确立了支付外币政府债务的临时程序,这一招被认为是避开美...
2022-06-24 09:09:00 -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出反诈利器 正式推出“反诈名片”服务
继“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和全国移动电话卡“一证通查”等服务之后,工业和信息化部再出反...
2022-06-24 09:07:00 -
阿富汗临时政府赈灾人员:地震灾区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
当地时间23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经过多方联系,对阿富汗临时政府信息和灾难沟通部的一位...
2022-06-24 08:54:00 -
青平:当好反腐斗争急先锋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提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
2022-06-24 08:51:00 -
青平: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要“三管齐下”
进入6月下旬,又到高校学生毕业时。今年高校毕业生数量在2021届的909万人基础上增加167万,预...
2022-06-24 08:51:00 -
青平:把握青年特质,更好满足青年成长成才需求
近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党的青年工作》出版发行。这部专题文集...
2022-06-24 08:51:00 -
青平:以“三个坚持”开辟人权事业新境界
近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2022-06-24 08:51:00 -
韩媒:韩政府着手在比利时设立常驻北约代表团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已着手在北约总部所在地比利时设立常驻北约代表团。韩外交部称,在韩...
2022-06-24 08:30:00 -
辽宁昨日新增7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均为丹东市报告
6月23日0-24时,辽宁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7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均为丹东市报告。...
2022-06-24 08:27:00 -
我国宏观杠杆率总体实现“稳字当头”
昨天(23日),“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近年...
2022-06-24 08:27:00 -
暴雨、大风、雷电齐聚!上海目前三个预警高挂
上海中心气象台2022年06月24日05时05分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较强雷暴云团影响,预计未来6...
2022-06-24 08:16:00 -
上海昨日新增本土“2+1”
2022年6月23日0—24时,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例和无症状感染者1例,均在隔离管控中发现...
2022-06-24 07:55:00 -
北京昨日新增本土1+2,在通州和东城,病例情况公布
6月23日0时至24时,北京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和2例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4例境外...
2022-06-24 07:55:00 -
欧盟批准乌克兰为欧盟候选国 泽连斯基:这是历史性时刻
综合报道,当地时间23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宣布,乌克兰和摩尔多瓦都成为了欧盟候选国。...
2022-06-24 07:54:00 -
放大招!福州:外地毕业生求职“包住一年”
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超过了一千万,即将走出校园的高校毕业生在忙着找工作的同时,也在到...
2022-06-24 07:34:00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843号